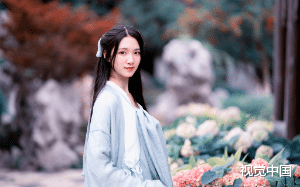我是相府千金。
曾是长安城中最令人艳羡的贵女。
在我及笄当日父亲带回来一个女子。
说她才是真千金。
后来。
我成了真千金身边最低贱的侍女。
只为再见母亲一面。
我是相府千金身边的侍女,卑躬屈膝。
她会踩着我的背骂我‘贱种’。
也会笑着让我喝下她的洗脚水。
人人都说,我是天生的下人命。
因为我毫无反抗之心。
她总喜欢让我去做任何事,事无巨细。
正如此时。
“丑奴,过来!”
顾芗娇声道。
她如今不过十五岁,却已初显倾城之姿。
我自觉跪下,爬到她身边。
她嗤笑一声,抬起脚踩到我的背上,语气凶狠。
“果然是下贱坯子,连烧个洗脚水的小事都做不好。”
说完,又一脚狠狠踹到我的腰窝。
我疼得匍匐在地,面目扭曲。
顾芗下了榻,走到我面前,用鞋尖勾起我的下巴,突然笑得异常温柔。
“丑奴,这洗脚水用来给本小姐洗脚是不能够了,你就喝了吧。”
我打了个寒战,爬起来低眉顺眼应是。
“是,小姐。”
说话间,整个屋子都静悄悄的,无人发出声响。
侍女们都见怪不怪了。
众人皆知,我虽然能进屋子里贴身伺候小姐,却也是整个院子里最低贱的侍女。
顾芗仍觉不够,踢翻了洗脚盆,水溅了我一身,用手帕捂着鼻子冲周围的侍女们吩咐。
“把丑奴拖到院子外跪着,没有我命令,不许让她起来!”
然后‘啐’了我一口,厌恶之意溢于言表。
“晦气东西!”
我没有挣扎,因为我知道没有用。
侍女们将我拖出去的时候,一路上,都有人在吃吃的笑。
幸灾乐祸的讥嘲不绝于耳。
我耷拉着脑袋,只当听不见。
我跪的地方正好旁边是一架秋千。
顾芗坐在秋千上,盯着我,眉眼阴沉。
“你昨晚半夜偷溜去前院是想做什么?”
我沉默着摇摇头。
她眯了眯眼,继续逼问。
“你是想去阿爹跟前装可怜,做回你的小姐?”
“还是,你想跟阿爹告状说我欺负你?”
倏地,她拽住我的头发,嘴角的笑寒意瘆人。
“再让我知道你离开这座院子乱说话,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不敢和她对视,只是一遍遍的磕头求饶。
“奴婢不敢,奴婢不敢。”
顾芗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也在我身上撒了气,自是万分满意。
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想说的话终究还是没说出口。
我想说,我不是去告状的。
我也不是想要做什么小姐。
我只是想求那个曾经被我唤作父亲的人。
让我再去见一见我的母亲,或者说,养母。
哪怕是在她身边,做一个侍女,也好。
冬日寒冷,雪越下越大,院子里渐渐地只剩我一人,其他的侍女们没得顾芗吩咐,没人敢搭理我。
只能任由我自生自灭。
院子里的积雪渐渐没过膝盖。
我还是没忍住,想起了从前。
我不叫丑奴,我叫顾岁岁。
那时,我还是金尊玉贵的相府千金。
长安城中人人艳羡的贵女。
父母虽严苛,却也慈爱。
将将及笄时,母亲就开始大张旗鼓安排。
小到宴席的饭食酒水,大到替我上簪的赞者,全都亲手操持,不假手于人。
侍女还凑趣说:“全京城再没有比小姐更有福气的姑娘了。”
我浅笑着,心里也是认同的。
可出现的变故让我始料未及。
及笄礼当日,府里闯入一个女子,指着我声音吼得撕心裂肺。
“她是假的!她不是相府的小姐!”
我愣在当场。这才发现,闯进来的人面容与我有几分相似。
她说,十五年前父亲的政敌趁着母亲产女混乱之际,用普通人家的女婴将相府千金调包了。
恍惚间,我只觉得荒谬至极。
那自称是相府真千金的女子站在厅堂中央,看着我怯生生的,眼神却没有丝毫躲闪。
今日宾客众多,且多是父亲朝中同僚,宴席中议论声渐大。
母亲在一边没说话,看着父亲当场滴血验亲,眼看着水中血液融合在一起。
而后,又拉着我同样的操作。
可结果截然相反。
我猛然看向母亲,想让她哪怕是说一句‘无论你是谁,都是我爱了十五年的女儿,’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就好。
可我注定失望了。
我只看见母亲向来慈爱的眼底,看着我是陌生的寒冷和浓烈的厌恶。
而后就给她安排了住处,事事过问。
至于我,在府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所有人都说,鸠占鹊巢的山鸡终究是成不了凤凰。
我耳边不再是阿谀奉承,只有数不尽的奚落和嘲讽。
……
耳畔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隐约中,我似是听到了父亲的声音。
彻底陷入黑暗前,我甚至还有些遗憾。
为何来的人不是母亲。
半梦半醒间,我听到父亲的声音。
“阿芗,你不要这么冲动,你要是把岁岁弄死了,会惹人怀疑的。”
“阿爹,你是不是可怜她了?”
面对顾芗的胡搅蛮缠,显然父亲早已习惯。
“如果她死了,只会引起夫人怀疑我们做贼心虚,她的血对我们有用。”
“如果岁岁一直活着,你既能折磨她,又能时时刻刻提醒夫人对你的亏欠。”
顾芗语气里仍带着些气愤,但也已经平静了许多。
可是,接下来一番话,让我几乎滚下床去。
顾芗还在不住的抱怨,又很得意。
“阿爹,您这法子真好,让我冒充相府千金,只怕您那夫人再怎么也想不到,我这女儿是假的,而她的亲女儿在给我当牛做马呢。”
我没想到,这所谓的真假千金竟只是来自于一场骗局,骗局的主导还是我的父亲。
我不敢想象,若是母亲得知真相,会有多难过。
我想要接近母亲的想法更强烈了。
只是我不明白,父亲策划这一场骗局的目的何在。
等我再睁眼时,父亲正站在我的床边。
“今日之事,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阿芗只是嫉恨你抢了她的身份想出口气,你就忍着吧。以后别出院子了。”
他的眼中一片阴霾,看着我像在看一个死人。
是了,他是高高在上的丞相大人,还策划了这场令我沦落至此的骗局,怎么会在乎我的死活呢。
他救我,不过是担心我的死会对顾芗不利罢了。
我仰头看着那个被我喊了十五年父亲的男人,想问他为什么。
可我不敢,我就是个胆小鬼。
我顺着他的意思乖巧应下。
“是,奴婢知道了。”
这一场折磨,让我躺在床上歇了半月有余。
后来,听说母亲病了,连在顾芗面前我也是心不在焉。
顾芗这次破天荒的没发火,她看着我,笑得不怀好意,“阿奴,你是不是也很担心母亲?这样吧,正好我这几日没空,你就去替我尽孝吧。”
我已经顾不得去想她在打什么鬼主意了,担心母亲的心占了上峰。
我急忙跪伏在地。
“奴婢定会完成小姐的交代!”
第二日,我站在山脚下。
眼前是蜿蜒而上的山路,坎坷崎岖。
顾芗的话还在耳畔回响。
“丑奴,听闻玉泉寺极灵验,只是得三步一叩首方可使自己的心意上达天听,正巧本小姐这几日不舒服,你就替我去了吧。”
她笑得花枝乱颤,看不出有哪里不舒服。
正值寒冬,山上更是寒凉。
身边一台又一台的轿子路过,都是城中的小姐们上山烧香。
凛冽的风顺着单薄的外衫钻进骨缝里,三步一叩首,膝盖和额头已然麻木,可我心里想的全是卧病在床的母亲。
即使见不到母亲,能够为她祈求身体康健也是好的。
等我回到府里,已是入夜。
顾芗的院子灯火通明。
隐隐有说笑声传出来。
我猫着腰进了院子,才发现是母亲在和顾芗说话。
我心下一喜,正要把怀里的平安符拿出来。
下一刻,顾芗的话就让母亲勃然大怒。
顾芗偎在母亲怀里,字字句句看似在诉说自己对母亲的仰慕之情,实则是在煽风点火。
“母亲,都怪阿芗身体不好,不能出府,只能在府里为母亲抄血经,不像丑奴,还能为自己的亲生母亲出府去庙里祈福。”
闻言,母亲捏着顾芗受伤的手指,满眼心疼,旋即又对我怒目而视。
对上母亲的眼睛,我本想辩解。
但母亲已是愤怒之极,冲到我面前,狠狠给我来了一耳光。
“来人,将她的平安符丢出外面去,莫要脏了院子和我的眼睛!”
我的脸颊火辣辣的疼,仆妇们撕扯着我,将平安符搜出来。
母亲看也不看一眼,就将平安符扔到火盆里。
平安符在火盆里一瞬间就化成了灰烬。
顾芗卧在房间暗处,神色诡谲,好似对母亲的反应早有预料。
玉泉寺之行的努力付之一炬,我毫无办法。
我想解释,解释我不认识自己的‘生母’,也只是为她祈福。
却不知从何说起,毕竟有顾芗的血经在前。
母亲只会心疼顾芗,也更相信顾芗。
彼时,我以为母亲只是因为觉得亏欠顾芗,才会对我如此苛刻。
不曾想,是顾芗透露给母亲,说她被掉包过去的,正是父亲曾经的青梅竹马的那户人家,得知自己不是亲生的,便动辄打骂。
这才让母亲对我态度大变。
毕竟女儿在情敌家受尽苦楚,而我,还享受了十五年的优渥富足的生活,更让母亲愤愤不平。
这日过后,本来看我就不顺眼的侍女更是变本加厉。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曾经高高在上的小姐,一朝跌落云端,谁都想踩一脚。
这日,我照例进了屋子里去伺候顾芗,顾芗却不像以往那般恣意。
她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慌张,嘴里还喃喃自语。
“怎么办,要是我被供出来这可怎么办。”
路上,我已听到侍女仆妇们都在讨论,巡逻的护卫抓到个意图翻墙的书生,已经扭送到夫人面前了。
据说不知是与哪位小姐约好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看这情形,不用猜就知道是顾芗胆大包天,竟勾了男子到家中花前月下。
我缩在一边,不敢出声。
蓦地,两道眼神落在我身上,我抬眼看去,是顾芗和她的侍女青萍。
他们盯着我的眼神发亮,青萍凑到顾芗耳边嘀嘀咕咕。
我的心脏不受控制的开始剧烈跳动。
没等我反应过来,母亲就带着一群膀大腰圆的仆妇进来。
扫视了一圈院子,语气严厉。
“阿芗,母亲这边抓到一登徒浪子,指控说是约了你院子里的小姐,还互许了终生。”
眼看着顾芗收敛了着急忙慌的表情,下一刻,天旋地转间,我就被拽着跪到了母亲面前。
顾芗哭诉的声音在我耳边炸开。
“母亲,是丑奴!刚刚我才审问出来的,丑奴说自己已经是那登徒浪子的人了,所以才互许了终生!”
闻言,母亲脸色大变,看都不愿意再看我一眼,撇过脸。
顾芗犹在哭泣,还不忘添油加醋。
“母亲不若饶了那登徒子,丑奴既是他的人了,身怀有孕也未可知呢?”
“总不能让孩子出生就没了父亲。”
我被仆妇按在地上捂着嘴,险些被顾芗冠冕堂皇的话气呕血。
为了给情郎脱罪,当真是不遗余力。
母亲的脸蓦地冷下来,蹙着眉吩咐身边的侍女。
“果真是土匪窝里出来的,半点羞耻心都没有!”
“去让府医熬一碗落胎药。”
而后看着我,像在看一团无用的垃圾。
“这样的孩子留着,没得辱没了相府的名声,若是我的阿芗被带累了,就是打死你也不为过!”
虽知道母亲是被蒙在鼓里,心口却仍是忍不住隐隐作痛,像被割开了口子不断有风灌进来。
曾几何时,我也是母亲尽心维护的掌上明珠。
这一切都被顾芗毁了。
被下人拖下去的时候,我用尽了力气,几乎就要挣脱控制。
眼角余光中,母亲看着我的眼神似是有一瞬间的松动,我心生希翼。
但顾芗枕到母亲膝上,不知说了些什么,母亲的态度重新变得冷硬下来。
我被拖到了下人房里,嘴里的破布被取出来。
很快,一碗药下肚。
仆妇们这才松开我,任由我瘫倒在床上。
为了方便伺候,所以下人房离顾芗的屋子很近。
近到我那莫须有的‘孩子’化成鲜血染红染脏被单的时候,我还能听到母亲在哄顾芗,温言软语。
肚子很疼,身下剧烈的疼痛告诉我,我的血要是再止不住,我恐怕就要命丧于此了。
母亲嫌弃我是土匪窝里出来的不干不净的话还盘桓在耳畔。
一时恍惚间,我竟觉得就这样死去也好。
可想到顾芗还在欺骗着母亲,我又生出了一点力气。
意识模糊之际,有人进来了,似是被我的惨状惊到,连滚带爬地跑了。
或许是母亲那无意中伤人的话,半梦半醒间,我再一次梦到了从前。
真假千金事件后,我在后院里成了无人问津的小可怜,不过,母亲仍未苛待我,只是不再如从前那般待我细致。
我以为,此生就会这样平淡的过去。
谁知父亲那早已落魄的政敌找了来,在去上香的路上,他挟持了顾芗。
那时还是秋日,他带着顾芗退到了悬崖边上,崖边古木的树叶被风吹得簌簌作响。
那人对父亲说,“你要想顾芗活命,就拿顾岁岁交换。”
想来此人恨极了父亲,想要看父亲陷入两难的境地。
一个是亲生女儿,一个是养了十五年的养女。
正常人都很难抉择。
我躲在人群后,看父亲取舍。
不成想,我的母亲,一把将我推到那人身边,那人顺势松开顾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