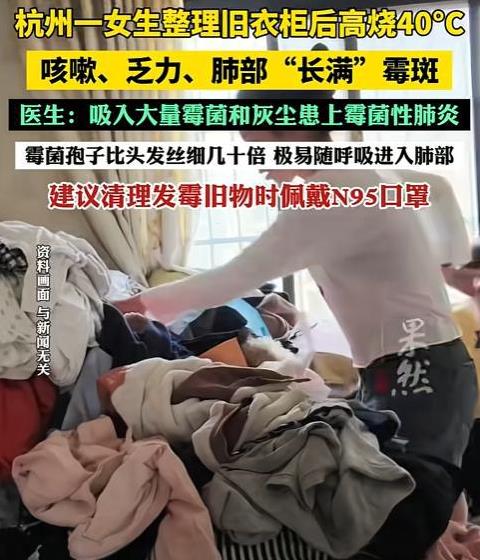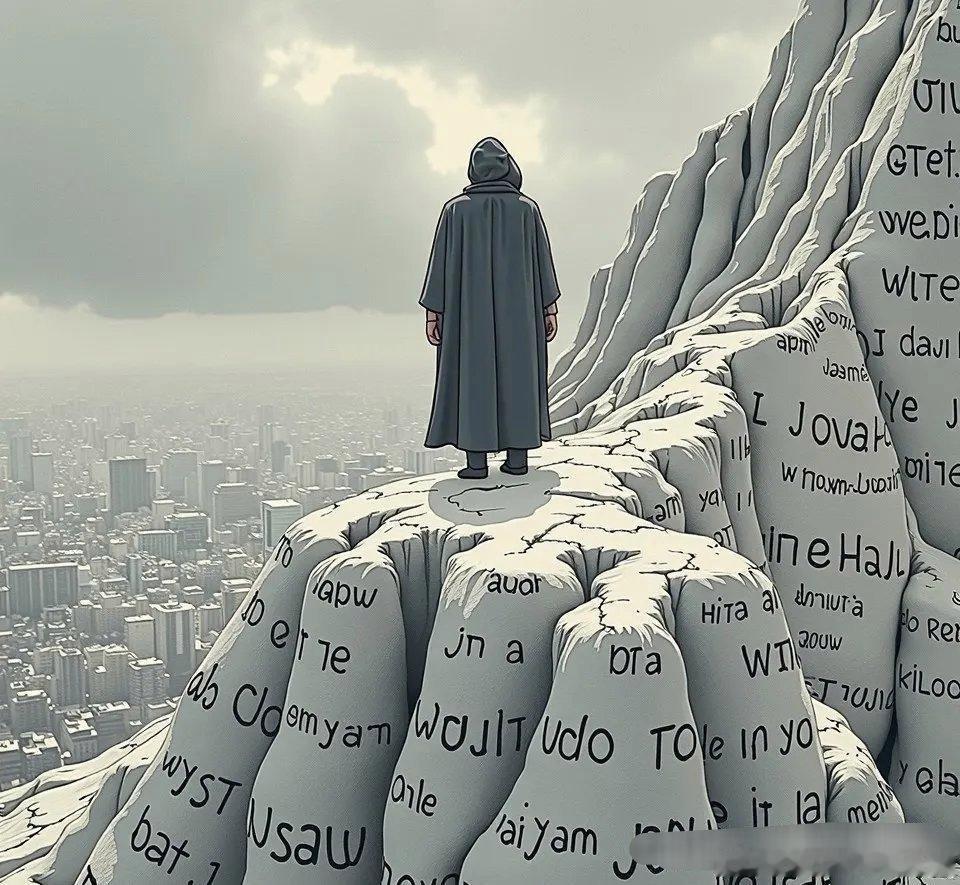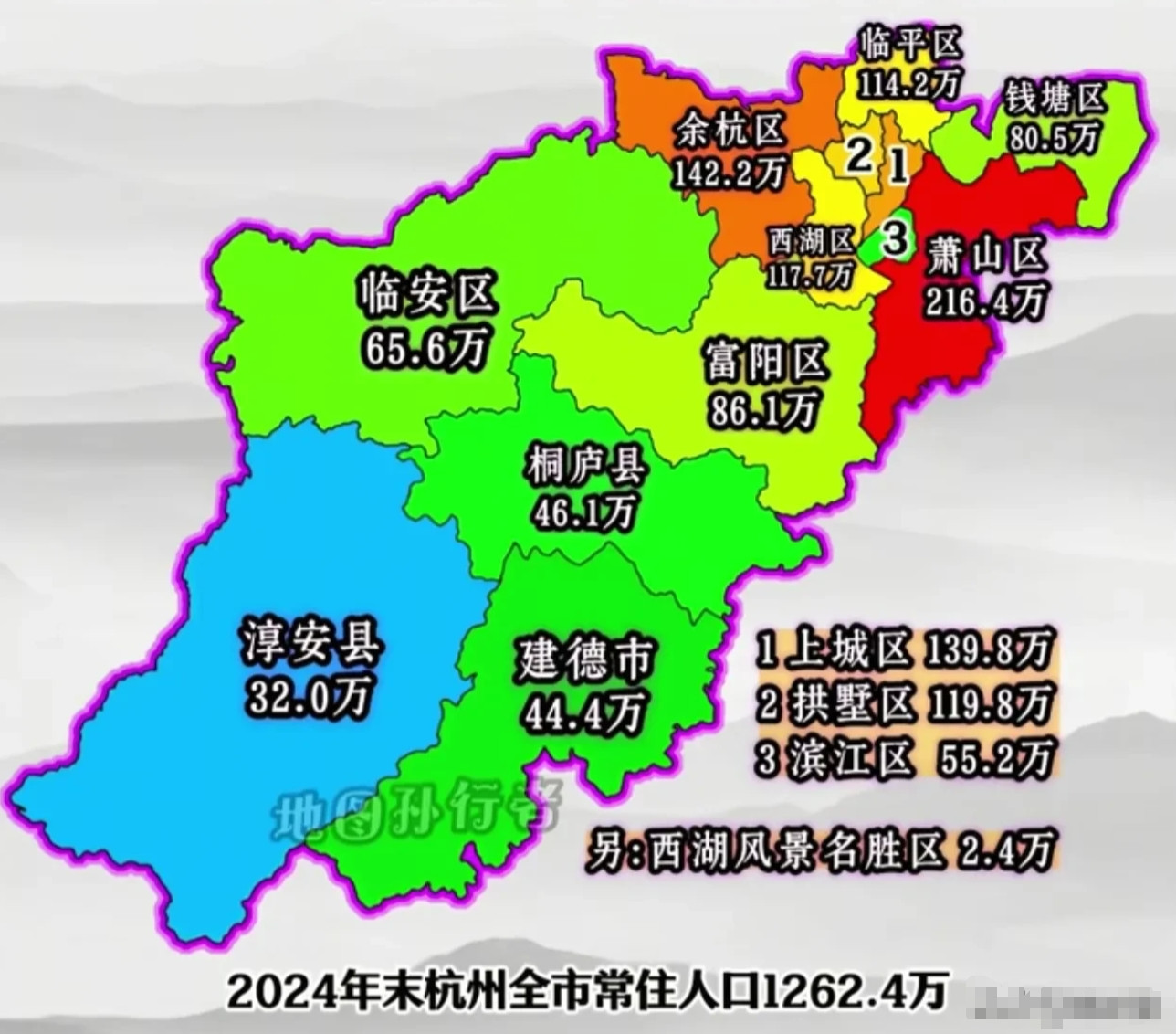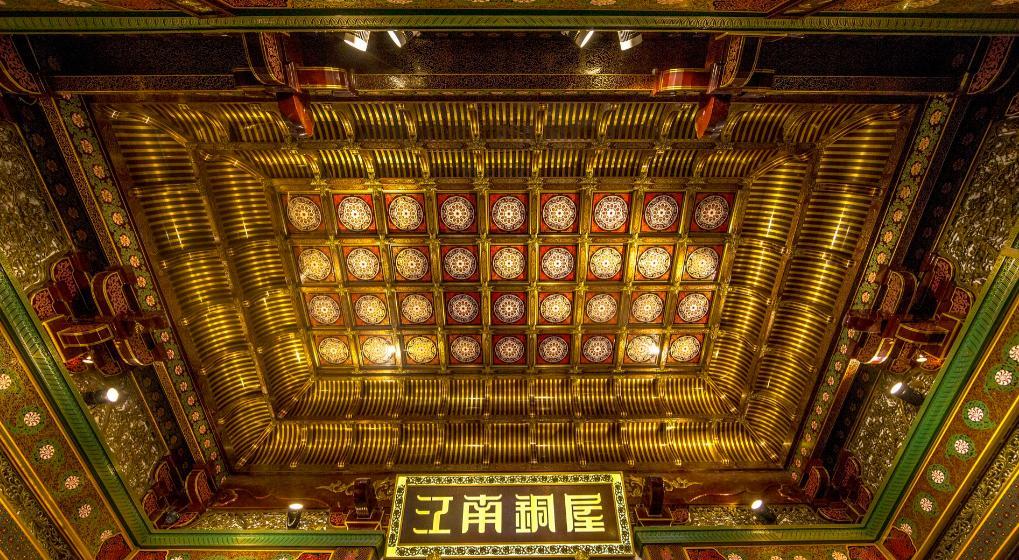在乾隆年间,杭州赵钧台去苏州买小妾,初见其容貌,甚是欢喜,可低头一看,顿时失望地摇了摇头说:“可惜,可惜。” “可惜,可惜!”茶楼雅间里,赵钧台盯着眼前佳人,嘴里连连叹息,旁边媒婆急得额头冒汗。窗外春雨细细地下着,敲打着青瓦,屋内却弥漫着一股微妙的尴尬。赵钧台的目光从李姑娘的脸缓缓下移,落在她裙摆下露出的那双脚上——没有弓鞋,没有三寸金莲,只有自然舒展的轮廓。 他眉头一皱,心里的算盘瞬间拨乱了。可这女子是谁?为何让这位杭州富商千里迢迢赶来,又为何让他如此失望?故事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那是个寻常的午后,杭州城里,赵钧台的绸肆生意清淡,他倚在柜台后打着盹。忽然,前厅传来几个客人的闲聊,声音不大,却字字钻进他耳朵:“苏州出了个李氏娇娘,模样俊俏,才情更是了得!”赵钧台一个激灵,瞌睡全无。 他虽已是妻妾成群,可对美色和才情的渴求从未减退。招呼伙计一问,得知这李姑娘名声早已传遍苏州城,连杭州都有了风声。他当即拍板:“备轿,去苏州!”伙计愣了愣,见老板兴致高昂,也不敢多问,麻利地收拾行囊,随赵钧台上了路。 一路风尘仆仆,到了苏州,赵钧台顾不上歇脚,就让伙计四处打听。没多久,消息传来:这李姑娘出身官宦之家,因家道中落,男丁被流放,她沦为官妓,却被伎倌妈妈收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如今刚及笄,一曲琵琶便名动全城。 赵钧台越听越心动,暗想:若能将此女纳为妾,既得美色,又添才情,何乐不为?他当即请来苏州最有名的媒婆——一个嘴角带痦子、眼珠子滴溜转的老妪,直言赎身银子不是问题,只求速成好事。 媒婆得了令,喜滋滋地跑去说合。伎倌妈妈却不急着应,反拉着李姑娘商量:“人家愿出重金赎你,可得先见一面,看看人品如何。”李姑娘虽不愿为妾,但也知自己处境艰难,点头应了。 见面定在城中一间茶肆,春雨绵绵,赵钧台特意换上最衬肤色的青衫,满怀期待推门而入。一眼瞧去,李姑娘端坐桌旁,粉裙白帽,气质如兰,长发如瀑,连身旁的丫鬟都透着灵气。他心头一喜,可目光下移,笑容却僵住了——那双脚,平平展展,竟未缠足! 赵钧台是个讲究的人,在他眼里,女子美貌固然重要,可若无“三寸金莲”,便少了那份婀娜风韵。他失望地摇了摇头,嘴里蹦出那句“可惜,可惜”。 媒婆见状,心知这桩买卖要砸,急忙挤出笑脸:“赵官人,您别只看脚啊!这姑娘才貌双全,诗词歌赋信手拈来,不信您试试?”赵钧台心想:娶是不可能娶了,不如逗她一逗,也算没白跑这一趟。于是他斜靠在椅背上,懒懒开口:“世间女子皆缠足,唯独你不从众,就以弓鞋为题,作首诗吧。” 李姑娘闻言,眼底闪过一丝怒意。她自幼饱读诗书,家道虽败,骨气未丢。赵钧台这话,分明是轻慢她,她岂能忍?可当面发作有失身份,她冷冷瞥了他一眼,接过丫鬟递来的笔墨,提笔便写。 墨迹未干,她朗声念道:“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声调清亮,字字如刀,直刺赵钧台心窝。 赵钧台愣住了。他虽爱小脚,却也知这陋习并无古制支撑,不过是南唐后主李煜喜看宫妃裹足起舞流传开来的风气罢了。李姑娘这诗,不仅骂他浅薄,还点透了缠足的荒唐根源。 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想发作又无言以对,只得匆匆起身,丢下一句“罢了”,灰溜溜离去。从此,他再不敢提买妾之事。 可这事并未就此平息。茶肆里的人听闻此事,暗暗传开,李姑娘的诗成了街谈巷议的谈资。有人叹她才情,有人赞她胆识,还有人开始低声议论:这“三寸金莲”,到底是美,还是累赘? 春雨停了,苏州城恢复了往日的喧闹。赵钧台回了杭州,绸肆生意照旧,可他再也不提纳妾的话。李姑娘依旧留在茶肆抚琴,名声却更盛。 缠足这事,早在南唐时只是贵族风雅,到清朝却成了女子命门。康熙曾下旨禁裹足,奈何民俗难改,直到民国才真正松绑。时至今日,回看那段血泪史,不过是男子审美加诸女子的枷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