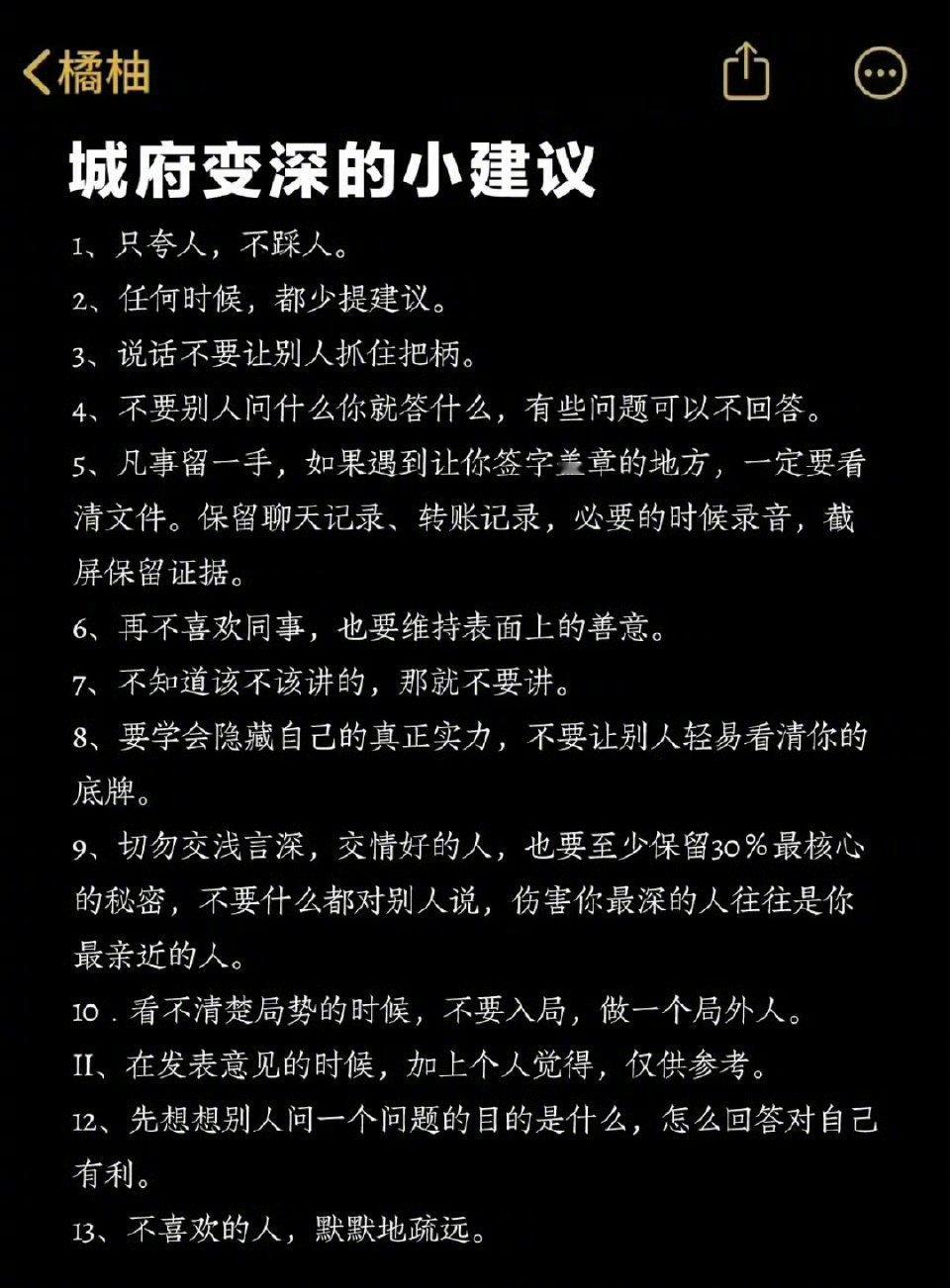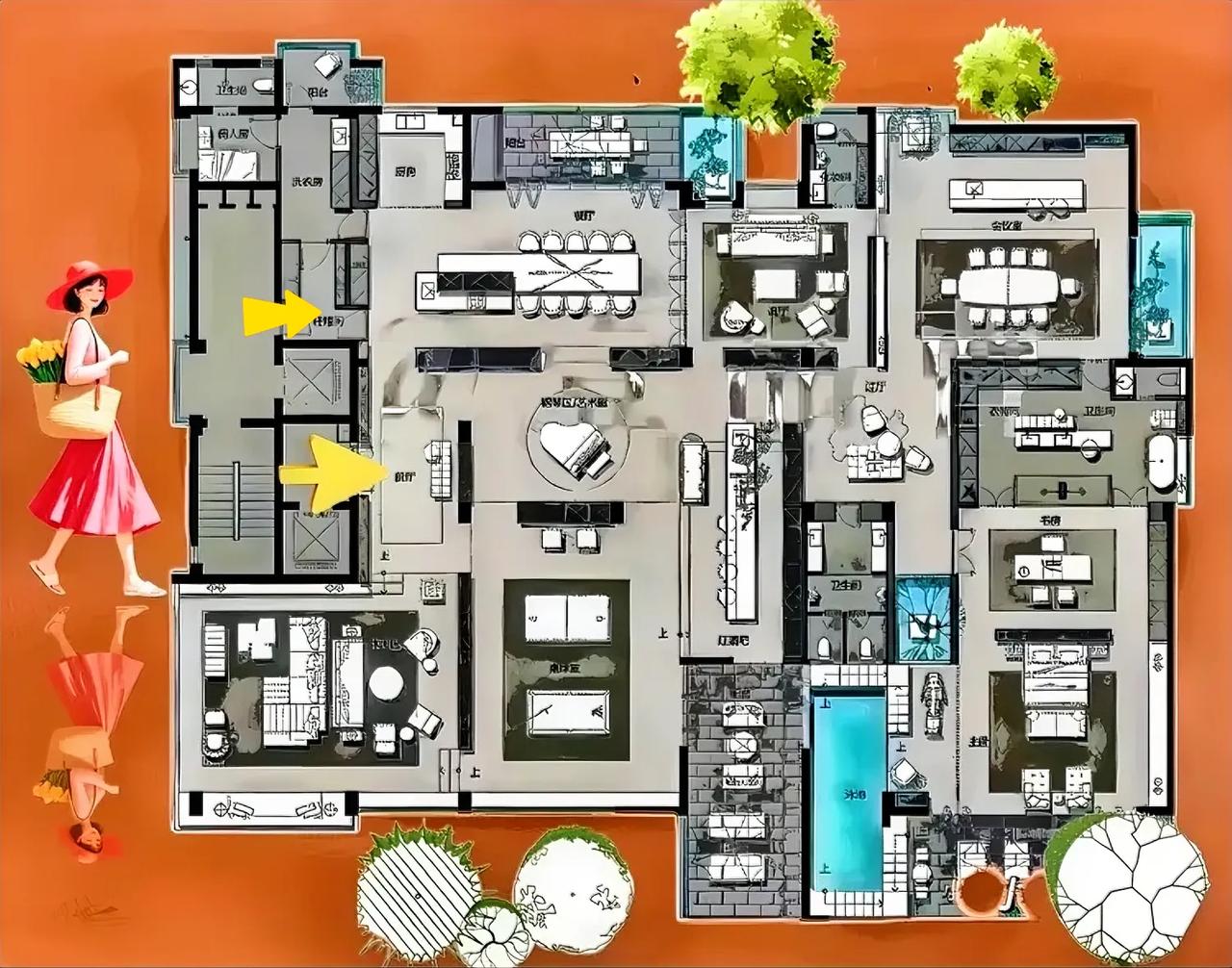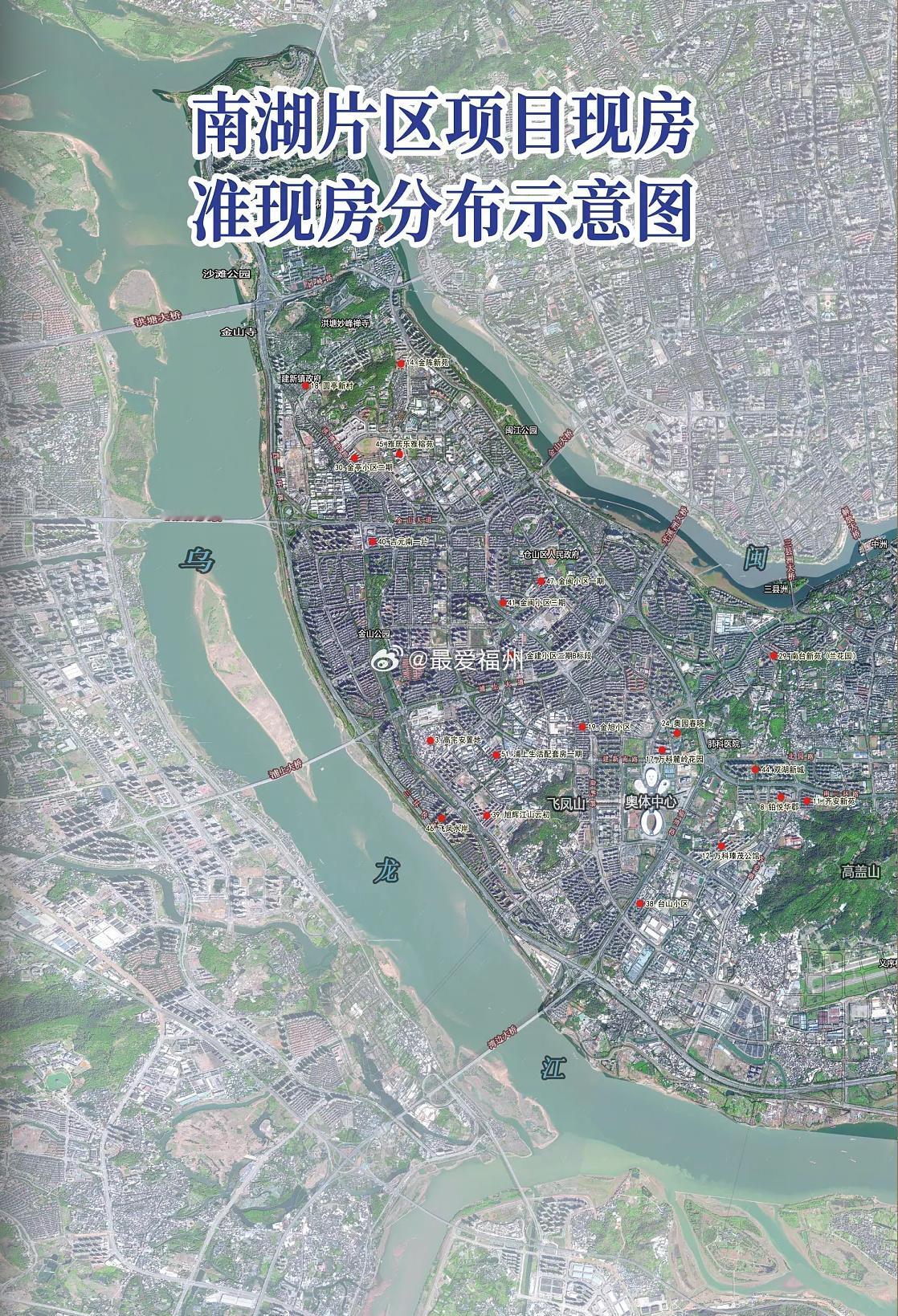1964年,被迫“退休”后的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郊外一所别墅内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他每个月有500卢布作为日常生活费,有时家里人还会来看他,他非常高兴,享受着天伦之乐。
1964年10月的莫斯科,秋风已起,叶子在风中打着旋落地,而赫鲁晓夫的人生,也迎来彻底转折。这个曾在苏联政坛雷厉风行、喊出“和平共处”口号、拍桌子敲鞋震惊联合国的人物,此刻,连自己下一顿吃什么都无法自主决定了。他的权力不是在战斗中输掉的,而是在看似波澜不惊的会议桌上,被一纸公文悄然抽空。
就在前几日,他还踌躇满志地谈论国家命运,在克里姆林宫的金色大厅里侃侃而谈,一边指点江山,一边翻阅文件,仿佛未来依旧在他掌控中。但这一切都变得如此突然。10月14日,他被指控“犯有主观主义和个人崇拜错误”,被“劝退”下台。
赫鲁晓夫被送往一处新别墅居住,从外表看去,房子既宽敞又典雅,有独立的花园,还有壁炉、书房,甚至一间专属的冥想室。但这里并没有他想象中的温暖与自由。屋内太安静了,安静得几乎能听见落尘的声音。他知道,某处的墙角,或许早就被克格勃的监听设备“照顾”周全。但这并不是他最担心的。真正让他难受的,是那种被世界遗忘的感觉。
权力离开的速度,比风还快。那些曾在宴会上向他敬酒、在会议上等他一句话拍板的大人物,现在一个个都如蒸发了一般,再未出现。连电话铃声也几乎绝迹,家门口不再有警卫,也不再有秘书来回传递公文。他成了一个被“隔离”的前统治者,被时代安放在了角落里,任凭他日夜徘徊,什么也做不了。
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时常一个人坐在窗前,望着空荡荡的庭院发呆。偶尔走到屋外散步,也只是机械地沿着小径走上一圈,然后很快折返。电视机成了他唯一的“陪伴者”,可无论是新闻还是文艺节目,他都提不起兴趣。
赫鲁晓夫也曾试图打破这份沉闷,他翻出旧时日记,回忆起当年从农民走到苏共中央核心的艰难历程,那段充满斗争与翻盘的岁月,曾让他无比骄傲。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在这个权力至上的体制里,一旦失去权位,个人也就随即被打入历史的冷宫。
到了年底,他和家人被“安排”搬进了另一处更加隐秘的别墅。外界称这是“妥善照顾”,可实际上,他心里再清楚不过,这是在隔离他和旧日政治生活的最后一道门槛。他慢慢意识到,自己并不被允许真正“退而休之”,他只是被悄然“处理”了。在这个体制下,没有荣耀的退场,只有悄无声息的消散。他曾是苏联的掌舵人,如今却只能每天为如何打发时间而苦恼。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不再掌握在自己手里,甚至连思想,也必须小心翼翼地收着,避免惹麻烦。 但赫鲁晓夫被迫"退休"后,每个月有500卢布作为日常开销,偶尔家人会来探望,令他感到十分欣慰,享受着天伦之乐。尽管如此,内心的落寞感却难以消解。 曾几何时,赫鲁晓夫是叱咤风云的苏联领袖。斯大林去世后,他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位期间力图改革,给国家带来巨大变化。然而,1964年,他却被勃列日涅夫等人赶下台,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与许多失势领导人的下场不同,赫鲁晓夫并未遭遇丧命或囚禁之灾。他被允许在莫斯科近郊安度晚年,过上了相对平静的退休生活。每天早晨,他都会在院子里锻炼身体,享受远离权力中心的宁静时光。 然而,长期身处政治漩涡的赫鲁晓夫,难免对这种平淡的生活感到不适应。他时常通过收音机和报纸关注国家大事,内心依然牵挂着祖国的前途。只是,昔日呼风唤雨的他,如今已无法再为国家做些什么了。 家人的关爱成为赫鲁晓夫晚年最大的慰藉。儿女和孙辈们时常来看望他,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共进午餐,其乐融融。天伦之乐抚平了赫鲁晓夫内心的创伤,给他带来久违的欢愉。 然而,仅仅依靠家人的关怀,并不足以完全填补赫鲁晓夫内心的空虚。他渴望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于是在家人的鼓励下,开始尝试写作。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坦诚地记录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从早年的革命经历,到成为苏联领袖后的重大决策,再到晚年的隐居生活,他毫无保留地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喜怒哀乐。他也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对国家未来的期许和忧虑。 写作成为了赫鲁晓夫晚年生活的重心。每天,他都会抽出几个小时专心创作,用笔墨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感悟。这个过程让他重新找到了存在的意义,仿佛又回到了昔日掌舵国家的时光。 然而,赫鲁晓夫的写作计划很快就被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知晓了。出于维护党和国家机密的考量,勃列日涅夫派人要求赫鲁晓夫交出手稿,并停止继续写作。这无疑是对赫鲁晓夫的又一次打击。 尽管受到阻挠,赫鲁晓夫并未完全停笔。他继续以更加隐秘的方式进行创作,只是这些作品在当时的苏联无法公开发表。 1971年,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7岁。虽然晚年的赫鲁晓夫远离了权力中心,但他对国家的关切之情却从未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