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医家费伯雄在论及风痹治法时,曾语重心长地提醒后学:“治风痹若不补血而先事搜风,犹如扬汤止沸,反使营血更燥、筋脉更拘。”这话背后藏着他对风痹病机的深刻洞察——看似风邪为患的关节病,病根儿却在血虚。
风痹发作时,患者常觉筋骨拘挛、关节疼痛,古人多从风邪侵袭论治,却往往忽略了“血不荣筋”这个关键。
费伯雄打了个比方:筋脉如同草木,若血液如同润泽的水土不足,草木便会干枯蜷曲,此时若再遇狂风(风邪),只会折损更甚。
肝主藏血、主筋,当营血亏虚,筋脉失去濡养,就像失去盔甲的士兵,风邪便乘虚而入,钻进经络关节,导致疼痛、活动不利。
这不是单纯的外邪致病,而是“内虚招邪”的结果,血虚是本,风邪是标,二者相互纠缠,形成恶性循环。
那么该如何破局?费伯雄提出了层层递进的治法:首重养血,次通络,再祛风。
他说“当以养血为第一”,就像先给干涸的土地浇灌,让草木恢复生机,才能抵御风雨。这里的养血不是轻描淡写地用几味补血药,而是“大剂补血”——重用当归、熟地、白芍这些能填补肾肝精血的药物,好比给身体输送“粮草”,让筋脉得到充分滋养,腠理致密,风邪自然难再深入。
待营血渐充,再佐以通络之品,如鸡血藤、桑枝,这些药能像疏通河道的工兵,让气血在经络中畅行,既助补血药发挥作用,又能带走滞留的病邪。
至于祛风药,如防风、秦艽,必须在养血的基础上谨慎使用,用量宜轻,且避开辛燥伤阴之品,以免刚补的营血又被耗伤,这便是“祛风又次之”的深意。
治疗阶段的转换也颇有讲究。初期好比“紧急救援”,先用大量补血药稳住大局,稍佐祛风药驱散浅表之邪;待营血渐复,便要“加固防线”,加入人参、茯苓、白术等补气药。
为什么?因为气血本是互生互长的关系,血虚日久必伤及气,补气不仅能助血生成,更能推动血液运行,好比给车辆加上引擎,让补进去的血能顺利到达全身。
同时,气足则卫外固密,能防止风邪再次入侵,这便是“营卫平调”的整体观——既补了体内的“虚”,又调了体表的“卫”,让内外和谐,病邪再无容身之处。
费伯雄的告诫在当时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他目睹许多医家一见风痹,便堆砌羌活、独活等辛散之品,虽能暂时缓解症状,却让患者越来越虚,关节越来越僵。
这种“见病治病”的短视,恰恰违背了中医“治病求本”的原则。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抓住了“血虚致痹”的本质,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理论推向更深层——不是简单的活血,而是从源头补足营血,让筋脉得到真正的滋养,再辅以通络祛风,使治疗既有层次,又无偏胜之弊。
如今看来,这套治法对慢性风湿类疾病仍有重要启示。比如类风湿关节炎、产后风等,患者常伴面色苍白、爪甲色淡、舌质淡等血虚征象,若一味祛风除湿,难免耗伤气血,加重病情。
遵循费氏“养血为先”的思路,重用当归、熟地,配伍温和通络之品,再根据病情轻重缓急调整补气药,往往能收到固本培元、驱邪外出的效果。这不仅是对古人智慧的传承,更是“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生动体现——治病如治水,既要疏导河道,更要涵养水源,方能正本清源,长治久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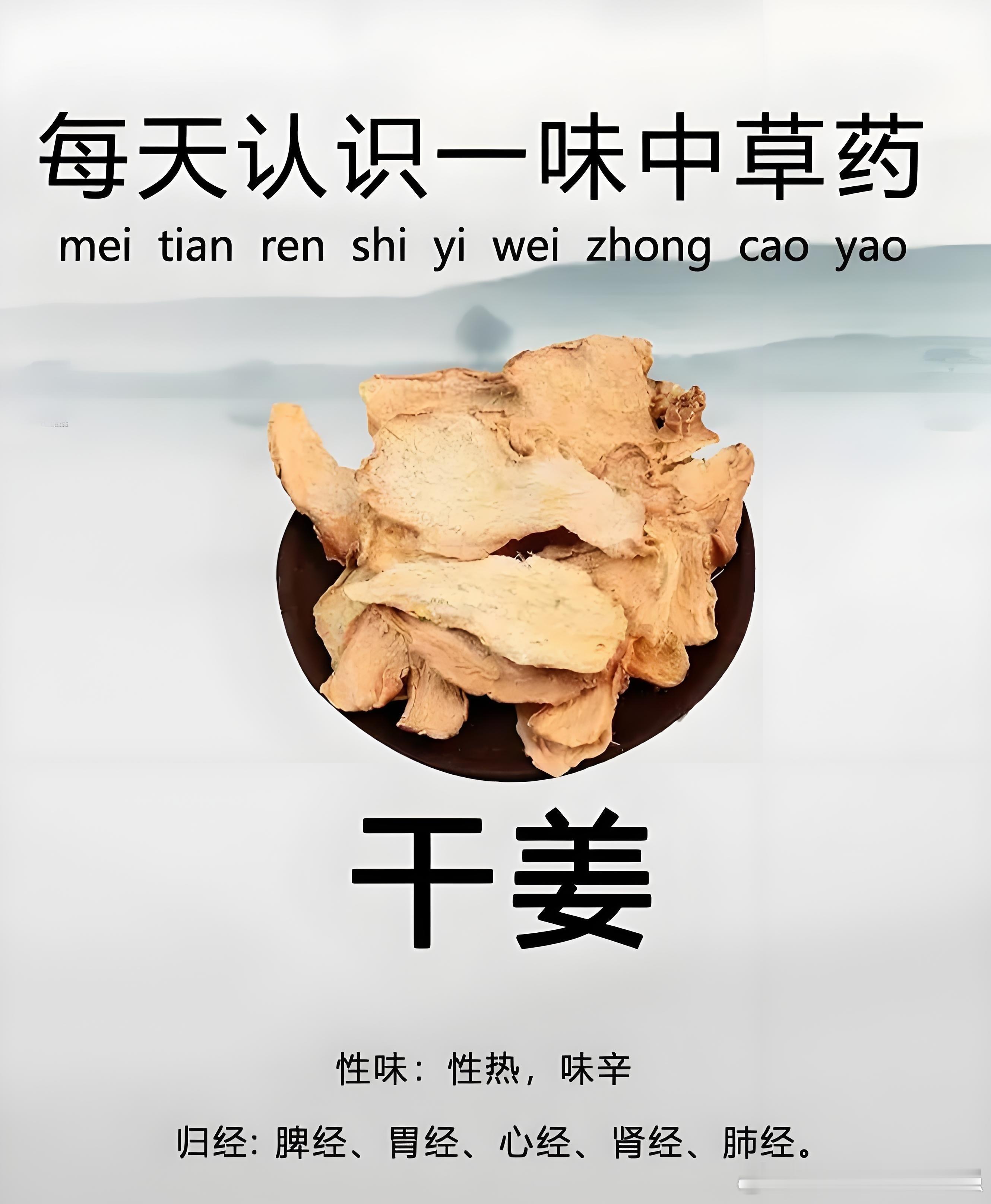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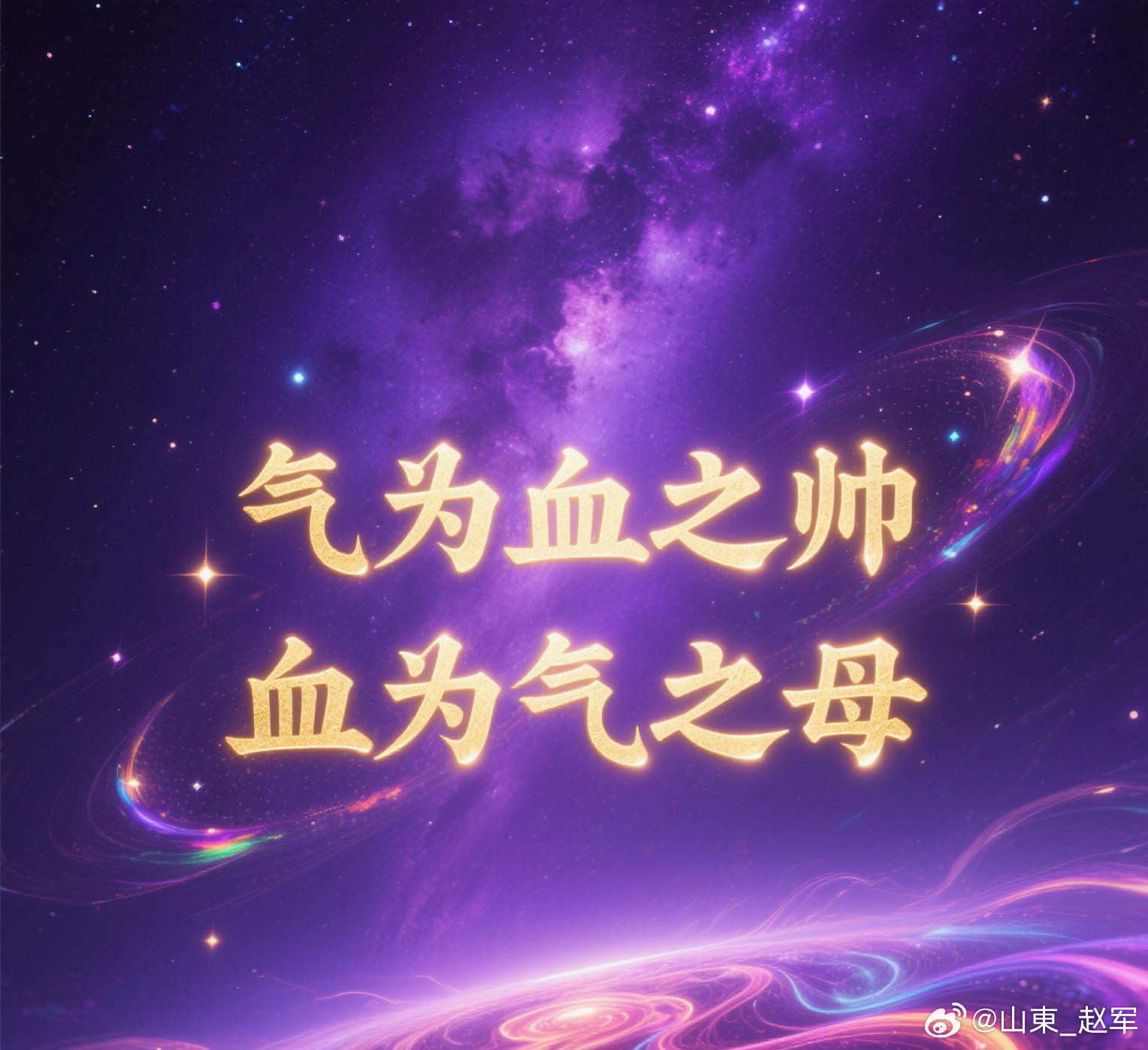


白山石
面色苍白、爪甲色淡、舌质淡等血虚征象,这样的症状,你告诉我先补血?六经八纲学到狗身上了么
李均
当归重了又拉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