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慎,表字谨庵,河北人,是个有钱人家的读书人。
有一年,他进京赶考,寄居在郊区的一所房子里。房子对门住着一位少年,生得眉清目秀,俞慎对他很有几分好感。一次,他们在门口偶遇了,俞慎便主动走上前去和少年攀谈起来。他看那少年对人很有礼貌,说话也很文雅,心里更是喜欢,就拉着他的手,把他邀请到自己的住处,用好酒好饭招待他。问起他的姓名,原来他也姓俞,名士忱,表字伺九,是金陵人。俞慎听到和自己同姓,觉得更是亲近,两人就结拜为兄弟。少年觉得俞慎是单名,而自己却是双名,就减去"士"字,单用一个"忧"字,叫做俞忱。这样,既是同姓,又是同一偏旁的名字,就越发显得像亲兄弟一般了。
第二天,俞慎到俞忱家回访。只见俞忱的书房和住室收拾得相当整洁,然而却静悄悄的,连个应门的老仆和端茶的书童也没有。
俞忱领着俞慎走到内室,叫出妹妹来拜见兄长。俞忱的妹妹名叫素秋,大约十三四岁年纪,模样生得很俊,细皮嫩肉的,就是雪白的玉石也比不上她的洁白。过了一会儿,素秋亲手端了茶来敬客,好像她家根本没有丫环。俞慎感到奇怪,只随便说了三两句话,就辞别了。自此以后,两人相处得像一奶同胞,十分友爱,俞忱没有一天不来俞慎的住处。有时天晚了,俞慎要他留宿,他总以妹妹无人做伴为由,不肯住下。俞慎很关心地对他说:"弟弟离家千里,流落外乡,连个接待客人的书童也没有。兄妹二人,又年轻,又柔弱,可怎么能生活啊!我想,不如同到我家,给你们一处房子住,怎么样?"
俞忱听了很高兴,约定等他考试后随他回去。
不久考试己毕,俞忱把俞慎邀到家里做客,他对俞慎说:"今天是中秋佳节,月明如昼,清光似水,不可不乐,妹妹素秋为你准备了一些酒菜,请不要辜负她的好意。"
说罢,拉着俞慎走进内室。素秋从套间走出来,向俞慎道了好,就又走进去,放下帘子,在里面整治饭菜。不大工夫,又亲手端出酒菜为二位兄长斟酒。俞慎很抱歉地说:"让妹妹来回奔忙,怎么过意得去?"
素秋没有答话,只是微笑,只见她刚返回套间,就有一个身穿青衣的丫环捧着酒壶,还有一个中年妇女端着一盘红烧鱼端到桌上来。俞慎很奇怪,问俞忱道:"这些人是从哪来的?为什么不早点出来侍候,却要麻烦妹妹呢?"
俞忱微笑着说:"妹子又作怪了。"
此时,只听素秋在帘内吃吃地笑,也不知在笑什么。到了散席的时候,那个丫环和那个妇女来桌边收拾杯盘碗筷。碰巧俞慎正在咳嗽,一时不慎,把一口痰吐到丫环的衣服上,只见那丫环竟随着唾声倒在地上,碗摔破了,菜汤撒下一地。低头一看,原来那丫环是一个用布剪成的人儿,只有四寸多长。俞忱见俞慎又吃惊又纳闷,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素秋也笑着从套间走出来,把布人拾了回来。不大会儿,那丫环又走出来,和以前一样进来出去拿取东西。俞慎依然呆在那里,俞忱这才向他解释道:"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不过是妹妹从小学会的用纸人、布人变戏法的小魔术罢了。"
俞慎见如此说,也便不再惊疑,就提起别的话来。他说:"弟妹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为什么还没有婚嫁?"
俞忱回答道:"父母去世之后,是留在这里,还是到别处去,连个定居的地方还没有定下来,所以婚嫁大事一直耽搁到现在。"
俞慎听了,立即同俞忱商量好起身回家的日期。于是,俞忱便将房子卖掉,带着妹妹随俞慎走了。
俞慎回到家里,叫人打扫出一处房子,把俞忱兄妹安顿下来,又派了一名丫环去侍候。俞慎的妻子是韩侍郎的侄女,特别喜爱素秋,每顿饭都要在一起吃;俞慎和俞忱也是这样。
俞忱天天在书房中陪伴着俞慎读书。他的脑子很聪明,读书时能同时阅读十行字,试着让他作了一篇文章,无论文才、结构,就是久经锤炼的老先生也比不上。俞慎见他文章写得这样好,就劝他去考秀才。
俞忱说:"我暂且陪你在一块读书,是想帮你消除寂寞,我知道我的福薄,不可能考中。况且,一经走上这条路,就不得不提心吊胆、患得患失,所以我不想参加任何考试。"
他们在一处同居三年,俞慎在考试时又落了榜。俞忱愤愤不平地说:"榜上挂一个名字,怎么就难到这个地步!我本来宁愿清清静静地活下去,也不愿为成败所迷惑。如今大哥的文才遭到埋没,实在令人不服,我这个十九岁的老童子,也要去试一试了!"
俞慎听到他也要去参加考试,非常喜欢。到了考试日期,亲自把俞忱送到考场,经过县考、府考、道考三级考试,都中了第一名。俞忱心中自然高兴,参加考试的劲头更高。回来后,与俞慎一道更加勤奋刻苦地读起书来。过了一年,二人一同去参加科试,又都得中了府、县的第一名。因此俞忱更出了名,远远近近有不少人家都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争着托媒来说亲,但是俞忱都拒绝了。俞慎竭力劝他,他只是说等会试后再说不迟。不久,会试完毕,仰慕他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来抄录他的应试文章,互相传诵,俞忱也满以为魁首在握。谁知等到放榜,兄弟二人竟都名落孙山。
当时,他们正在书房对坐吃酒,突然听到落榜的消息,俞慎还能强打精神,像是满不在乎地大笑着;而俞忱却大惊失色,手中的酒杯也掉在地上打碎了,身子不由自主地跌倒在桌子下面。俞慎把他扶到床上,见他病得十分危险,急忙将素秋喊来。他这才睁开两眼,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对俞慎说:"我们二人的交情,虽然像同胞兄弟,其实并非是同族。小弟自己感到很快就要去做鬼了,你待我兄妹的大恩也无法报答。素秋已经长大成人,嫂嫂既然很爱她,就让她给你做二房吧!"
俞慎嗔怪地说:"弟弟,你真是胡言乱语!我怎么能那样做,岂不是叫人骂我衣冠禽兽?"
俞忱听了,感动得流下泪来。他让人把自己抬进屋子,强打精神躺进俞慎用高价给买的棺材里,嘱咐妹妹说:"等我咽了气,就把棺材盖好,千万别让人看。"
俞慎还想和他说什么,已经来不及了。俞慎见俞忱突然死去,悲痛得真像死了亲兄弟一样。但是,心下又暗暗怀疑他向妹妹嘱咐的话有点奇怪。因此乘素秋外出时,揭开棺盖看了一下,只见棺材中光堆着一堆衣服,却不见了尸体;再揭开衣服一看:一条一尺多长的蠢鱼,直挺挺地僵卧在下面。俞慎正在惊异,素秋已急急忙忙地走进来,她看到俞慎将棺盖揭开了,便十分悲痛地对他说:"你们两个情同手足,自然也就无需避忌了。所以不让人开棺,并不是为了避你,但恐传扬出去,我也不能在你家久住了。"
俞慎很坦然地说:"一切礼节,都是根据人情来制定的。只要感情真挚,即非同类,也没有什么区别。妹妹难道还不了解我的心吗?就是你嫂嫂,我也绝不会向她泄露一句的,请你不要忧虑。"
为了免于拖延暴露,就很快决定了埋葬的日子,很隆重地把俞忱安葬了。
俞忱活着的时候,俞慎就想把素秋嫁给一家富贵人家,可是俞忱不同意。他死后,俞慎又和素秋商量,素秋只是低着头不言不语。他很庄重地对素秋说:"妹妹已经二十岁了,这么大还不嫁人,人们不是要说我的闲话吗?"
素秋说:"要是那样,我一定听从您的意见。可是我不愿嫁给富贵人家;要嫁,就嫁一个穷书生吧!"
俞慎说:"可以。"
素秋嫁人的话传出不几天,说媒的人相继而来,但素秋都不中意。
先前,俞慎的小舅子韩荃来吊丧,见素秋人才出众,很喜爱她,想买她做姨太太。他和姐姐去商量,姐姐急忙告诫他:"别再说了,恐怕你姐夫知道了,要发脾气的。"韩荃回去后,还不死心,就托媒婆径直向姐夫去说,并承诺在姐夫考试时,给姐夫疏通关节,保证考中。俞慎听了,勃然大怒,大骂一顿,把媒婆赶出门去,从此就和韩荃断绝了来往。
后来,又有个名叫某甲的,是已经去世的老尚书的孙子,因为未婚妻死了,也托媒人来说合。某甲家宅第连云,十分富有,这是人们平素就知道的。可是,俞慎还想亲自看看他的人品,就和媒人约定日期,让某甲亲自来一趟。
约定的日期转眼就到了。俞慎让人把内室的门帘放下来,让素秋在帘内相看。不久,某甲来了,只见他穿着贵重的皮袍,骑着高大的骏马,还跟着很多随从,向乡党夸耀自己的富有,而他的长相也很秀雅白净,和一个未出嫁的大姑娘一样。俞慎见了很高兴,可是素秋却不大乐意。也是俞慎一时糊涂,竟许下这门亲事,张罗着为素秋备办丰盛的嫁妆。素秋制止他,他也不听,给素秋陪送了很多东西。
素秋出嫁后,夫妻相处得倒也和好,只是非常想念兄嫂,每月总要回来一次,而每次来的时候,又总要从妆奁中拿回几件珠钗、绣衣之类的东西交给嫂嫂保存。嫂嫂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也暂且由她。
某甲少年丧父,又因母亲过于溺爱,无人管教,因此常常和坏人接近,被引诱得吃喝嫖赌,学下一身毛病,借下许多外债。为了还债,他把祖传的珍贵书画和金银器皿都拿去卖了。韩荃也和他认识,每日请他吃酒,暗中探试他对素秋的感情,渐渐地向他提出:愿意用两个姨太太和五百两银子和他换素秋。起初某甲还不肯,经不起韩荃的死磨硬缠,心里有些活动了,只是担心俞慎不肯甘休。这时韩荃又花言巧语地对他说:"俞慎和我是郎舅至亲,况且素秋又不是他家的人,事情当真办成了,他也拿我没有办法。万一他要出面阻拦,一切由我负责。此外,还有我父亲给我撑腰,还惧怕一个俞慎不成!"说罢,就让他的两个姨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到桌前来给某甲斟酒,又对某甲说:"你果真能照着我的话去办,这两个女子就是你的人了。"
某甲觉得用一个妻子能换到两个女人,而且还能得到五百两银子大赌几场,倒也痛快,就满口答应了,并约定了交换日期,然后辞别出来。
到了约定的日期,他怕韩荃欺骗他,就到半路上去等候。等了不久,果然有乘轿子来了,他掀开轿帘,看见轿中人果然不假,就领着她们回家,暂且把两个人安置在书房里。等韩荃的仆人又将五百两银子当面交清后,他才跑进内室证骗秋说:"你哥哥得了急病,派人来叫你了。"
素秋听了,心急如火,顾不得梳妆,急急走出门来,上了轿子。因为月暗路黑,轿子启程不久,就迷了方向。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多久还没有到家。就在这时,忽然看见两支巨大的蜡烛迎面而来,韩荃的仆人们心中暗暗欢喜,以为可以向拿蜡烛的人问路。及至走到跟前,原来是一条大蟒,瞪着两只像灯一样的大眼,闪闪发光。众人大惊,害怕被蟒吃掉,便把轿子往路边一扔,跑散了。天亮的时候,韩家的人才又聚集到轿前来,打开轿帘一看,竟是一乘空轿。他们想着素秋必定被蟒吃了,就抬着空轿回去向主人报告,韩荃听了,也只有垂头丧气而已。
几天以后,俞慎派人来看望素秋,才知道素秋被坏人骗走了,并没有怀疑到是某甲搞鬼。直到陪嫁的丫环回来,仔细问过,才对事情的始末有个大概了解。俞慎愤怒极了,跑遍县、府、省直至京都,到处去告状。某甲很害怕,就向韩荃去求救,韩荃因为人钱两丢,正在悔恨,所以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把他撵出门来。某甲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而这时各处衙门又都派公差拿着拘票来传他,他只得用银钱贿赂公差,才暂时没被带走。仅仅一个多月,为了向官府行贿,他把家里的珠宝、衣物和首饰变卖得一千二净。
俞慎在省里的按察使衙门追究得很急,府、县官员都得到严厉的命令,务必将
某甲拘捕到案。某甲知道不能再躲避了,才自动到公堂,招供了实际情况。按察使又发下拘票,要拘捕韩荃去和某甲对质。韩荃也害了怕,只得把作案的经过告诉了父亲。那时,韩荃的父亲韩侍郎已告老回乡,很恼怒儿子的不法行为,就亲自把韩荃绑了,交给公差。到了官府,韩荃招供了遇蟒的变故,主审官说他是借故支吾,把他连同仆人狠狠地打了一顿。这时,某甲也屡次受到严刑拷问。幸而韩荃的母亲卖去房产土地,上下行贿,韩荃才得以苟延残喘,而他手下的仆人却一个个都被折磨死了。
韩荃挨不过长期蹲监狱的苦楚,愿意帮助某甲一千两银子,让他出面哀求俞慎撤销这个案子。俞慎不答应,某甲的母亲又请求再加送那两个姨太太,只求不要再到官府去催促,暂且当作一件疑案,让他们慢慢去找寻素秋的下落。这时,俞慎的妻子韩氏受了她叔母的嘱咐,天天劝解丈夫,为韩荃开脱。俞慎这才答应了不再去催案。由于某甲经常吃喝嫖赌,再加上打官司的巨大花销,家中已经破产了,想把仅留的住宅卖掉,以凑足送给俞慎的银子,而当下又卖不了,就先把两个姨太太送来,乞求缓期交银。
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俞慎正在书房坐着,忽见素秋和一个老婆子走进来。他吃了一惊,急忙迎上去说:"原来妹妹并没有被蟒吃掉啊?"
素秋笑着说:"那条蟒,不过是我变的戏法。那天夜里,我逃避到一个秀才家,和他母亲住在一块儿。那个秀才也认识你,现在就在门外。"
俞慎听说是个熟人,顾不得穿好鞋子就出去了。一看,原来是宛平名士周生。他握着周生的手一同来到书房,立即叫人摆了酒宴,互相说起心里话来。说了半天,才弄清了素秋遇蟒前后的全部经过。
原来,素秋变的大蟒把韩家的人吓跑后,拂晓时候来到周生门前,叫开了门。周母把她迎进屋去,细细问了一番,才知道是俞慎的妹妹。周生当下就要派人去通知俞慎,素秋不让,就和周母住在一起。周母很喜欢素秋,想把她娶来给儿子做妻。但素秋对周母的每次试探都借口没有得到哥哥的同意,不敢答应。周生也认为自己和俞慎交好,不能在没有媒人的情况下马马虎虎地结合,只好先一次又一次地派人探听诉讼的结果。当听到诉讼已经过去时,素秋就要告别周母回家。周母让周生带一个老婆子去送她,嘱咐老婆子就便做个媒人。俞慎听了这番话,又因为素秋已在周家住了段时日,互相都有个了解,也有把素秋嫁给周生的意思。后来,听到老婆子要为他们做媒,心中很是高兴,就和周生当面定了亲。
素秋是夜里回来的,别人都不知道。她想让俞慎拿到银子后再对别人说,俞慎不肯这样办。他说:"以前,我的忿气无处发泄,想借索取他们的银子叫他们也尝尝败家的苦头。今天,我又见到妹妹,便是很大的安慰,这是万两黄金也难以换到的啊!"
随后,他就自动撤销了诉讼并正式通知了韩荃和某甲两家。
俞慎顾虑到周生的家庭不怎么富裕,道路又远,迎亲实在有困难,就把周母迁
到自己家来,让周家住在俞忱住过的院里。周生也随着风俗赠送了彩礼,请上吹鼓手,欢欢乐乐地举行了婚礼。
一天,嫂嫂和素秋开玩笑说:"你今天有了新女婿了。从前和某甲的枕席之爱,还记得吗?"
萧秋回头看着丫环笑着问:"记得吗?"
这下倒把嫂嫂弄糊涂了,就向她们追问究竟。原来,素秋在某甲家的三年,枕席上的事都让丫环来代替,每到夜晚,素秋就用笔给丫环画了眉毛,让她上床去陪某甲,自己对灯独坐,某甲也分不清是谁。嫂嫂听了,更是感到奇怪,就要求素秋把所会的魔术传给她,素秋只是笑着,不肯答话。
第二年,是三年一次的大比之年,周生要随俞慎去参加考试,素秋认为周生不必去,俞慎竟强拉着周生走了。放榜时,俞慎考中了,周生落了榜。又过了一年,周母逝世,周生就再不参加考试了。
一天,素秋忽然对嫂嫂说:"前些日子,你要我把魔术传给你,我本来不肯拿这些邪魔歪道吓人。今天我们将要远别了,让我秘密教给你,也可以用来避避战火。"
嫂嫂很吃惊地向她询问缘故,素秋答道:"三年后,这个地方要遭战乱,人们死的死,跑的跑,恐怕要没有人烟了。我的身体很柔弱,受不得惊恐,将要到海边上去隐居。大哥是留恋富贵的人,不能和我们同去,所以向你诉说这离别的话。"
说罢,就把她的魔术都教给了嫂嫂。几天后,素秋又来告别,俞慎再三挽留也留不下,竟急得流下泪来。问她到什么地方,她又不回答。
公鸡刚叫过,周生夫妻就早早地起来,带着一个白胡子老仆骑着两头毛驴走了。俞慎暗中派人在后边紧跟着去护送,到了胶州和莱州两地的边界上,忽然尘雾遮天,对面不见人。等到天色晴朗时,已经不知道他们往哪儿去了。
三年后,李闯王起事,韩夫人用布剪了个人物,放在大门内。义兵们来了,看见在这个院子的上空站着一个一丈多高的杀气腾腾的天神,四周都被白云围绕着,谁也不敢过去。就是用这个法子,才保住俞慎全家平安无事。
后来,村里有个商人到海边去做买卖,偶然遇见一个老头子,相貌很像俞家的那个老仆人,但是头发和胡子却变黑了。商人正在注目打量他,老头子停下步来对商人笑着说:"我们的俞公子还健康吗?请你给他捎个口信,素秋姑娘也很安乐,请他不要挂记。"
商人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老头子连连说:"远得很,远得很!"说罢,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俞慎听了商人的话,派人到海边到处寻访,也没打听到他们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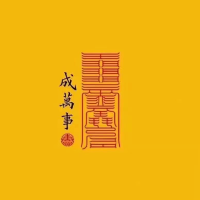
好故事[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