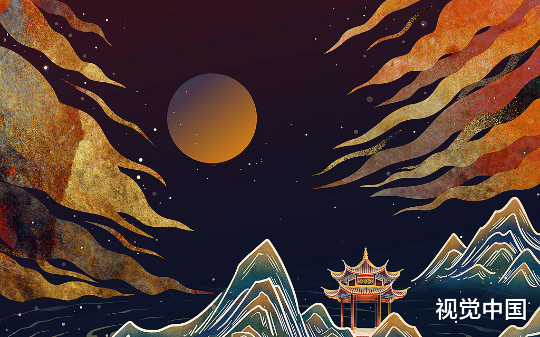新婚之夜,相公不肯碰我,七日后,我年过半百的婆母被诊出有孕
我知道,她怀的不是老爷的孩子,而且注定是个死胎。
看着我的相公既忧心忡忡又满目期待的样子,我低下头,掩藏起笑意。
这一切,就是我嫁入这阴森诡秘的齐家的目的。
人尽皆知,城中首富齐家供奉稻草人视作家神。
他们不知道的是,齐家正妻若非有孕进门,就要被送到祠堂,接受家神考验。
齐家昌盛百年,却从未有过通过家神考验、还不死不痴的女人。
而我,是即将嫁入齐家的齐彬正妻。
嫁到齐家的第一天,我独自跪在祠堂中间的簸箕上。
祠堂门窗紧锁,神龛上的稻草人如同有了神智一般,晃晃悠悠,无风而起,向我砸来。
血液喷涌而出,撒在我的嫁衣,一片鲜红。
1
今天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新婚之夜。
仆从散尽,红烛熄灭,我放下女儿身段,主动攀上男人的后背,要与他饮下交杯。
任凭我温言软语,他却像死人一样毫无反应,被我扰得烦了,他才转过身来撂下一句,
「大家闺秀都像你这么自轻自贱吗?」
我从床榻上起身,面无表情地扇了他一个巴掌。
我的声音是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阴冷:「这话的意思是,你还和哪个大家闺秀洞房花烛过吗?你敢对着你们齐家的家神发誓吗?」
他被这一巴掌扇蒙了,怒火腾腾,却也只是瞪视着我。
我亦不落下风,冷眼相视道:「你别忘了,我是奉天地祖宗之命,受你们齐家家神考验而出的正房夫人。齐家家规,如无家神批准,休妻必遭天罚。」
他狠狠地一拍床板,指着我的鼻子,「悍妇!如果不是你姐姐,你以为我会娶你吗?」
大抵是因为家神的考验,我到底算是作弊,因此难以拿起威势。
知道这杯酒他不会饮下了,我有些颓然地告罪出屋。
我知道他怨我。
毕竟齐家夫人的位置,是我朝思暮想,千方百计才得到的。
他不懂我的爱,不懂成为齐家夫人对我来说多重要。
他也不懂我的怨,怨他不放下姐姐。
怨他,因为他,我期盼许久的大婚之日竟然如此荒唐。
没错,我的成婚礼不是和齐彬,而是和齐稻度过的。
别误会,齐稻不是人,是一个稻草人。
也是齐家的家神。
当年齐家还未发迹,恰逢大灾之年,饿殍满地,贼寇横行,为防止贼寇抢掠,齐家的老祖宗每晚在睡前,都会从已经变成荒地的稻田里把稻草人拔出来,摆在自家门前,做出一副家中人口早已逃荒,屋内无人无粮的架势。
但齐家和周围的邻居相比到底还是算殷实,装作家中无人这一招对付得了外来的贼人,对付不了身边的祸心。
一天深夜, 同村的贼人觊觎齐家的金钱,准备谋财害命。扒着门刚准备闯入,隐约间看到一个人影在黑暗中静静的注视着他。
贼人仗着自己有几分蛮力飞扑过去,却因脚下不稳,被对方压倒。
这时他才发现那个立在那儿的并不是人,而是稻草人。
奇就奇在那稻草人虽扎得高大,但也不算离谱,不过是比一人高些。用稻草扎成,还需要每日搬动,能有多沉?
可贼人一个壮年男子,却无论如何都挪动不开。
次日清晨,齐家老祖宗转醒时,看到的就是在门前被稻草人重压了一夜,窒息而亡的贼人。
那贼人绝对挣扎了许久,气绝身亡了手里还握着用来行凶的匕首,而稻草人的身上也被捅出了好几个洞来。
但依然无济于事,贼人被活活压死。
齐家老祖宗将稻草人搬起之时,齐家人却又发现稻草人的重量并无问题。深感神奇之下也感谢稻草人的救命之恩,将稻草人视为家神供奉,献名齐稻。
那稻草人也仿佛真有灵性,十年后,老祖宗的孙子高中状元光耀门楣。
齐家自此风生水起,世代从政经商,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城中的大户,地位显赫。
这个故事我在进齐家门之前就知道。
因此,每日瓜果梨桃流水般的供奉,我能够接受。
每逢年节对着家神三叩九拜,我也能接受。
只是齐家不知道哪代起定了规矩,为了世世代代得到稻草人的庇护,凡齐家子孙成婚时,新娘会被先送到祠堂,和齐稻祝祷,甚至在大婚当天,要和齐稻拜堂,以彰诚心。
2
我记得我来齐家那日天气寒冷,我从家乘轿出发,进了齐家,没有和郎君相会,没有敬奉公婆,而是直接被送到了祠堂。
他们说,和齐稻祝祷的仪式很重要。
就连拜堂迎亲都要放在这诡异的仪式后七天。
但我没有异议,只是乖巧地按照老夫人的吩咐,跪坐在簸箕上,仰望着佛龛上的齐稻。
经过多年的修缮,齐稻早已没了什么稻草人的样子,反倒像是个稻草制成的塑像。
齐稻身形高大,比我高了足一个头,组成身子的稻草被精心地修剪过,外面套着丝绸的大红衣衫,却并不显得牵衣肘见,反而衣冠济楚、十分自然。
稻草人的头则是金丝楠木制成的,四四方方的头硕大不已,正面用朱砂和金粉在木板上勾画出五官。
即使能看出用心和造价不菲,但依然改变不了丑陋诡谲。
看着板子上那诡异的脸,我努力地挤出一个笑来,给齐稻正了正衣摆。
祠堂内红烛高照,我和那可怖的稻草人皆是一袭红装,仿佛我们才是今日成婚的新人。
原本站在一旁,远远看着我的齐家老夫人满意地走过来。扶着我的手,轻拍,「到底是你,不是你姐姐。你知道我原本就更属意于你,可不要让我失望,要快点给齐家开枝散叶啊。」
我笑了笑,避开齐稻的假脸,冲着老夫人保证:「我对齐彬之心无人可比。」
簸箕上虽有个垫子,但这个「规矩」本意就是磨新妇的性子,在祠堂的分分秒秒都宛如上刑。
……
虽是午后,但天色很黑,外面下着雹子。
噼里啪啦地声响重得很,格外让人心烦。
老夫人借口天色不好,身体不适,早早便离去了,却并不告知我要在这里待多久。
她一走,祠堂的大门就被外面的护院关上,不久,门口的站岗的人说了句外面的灯被风吹灭了,自己再去拿一只来,便也走了,半天也没有再回来。
我只能自己拖着跪了太久,已经没有知觉的下半身,挪动着去换蜡。
烛台上,蜡油淌了一地,长而尖的的蜡钎上空空荡荡。
那些人没有留蜡给我。
今天注定是黑的。
这可能就是下马威吧,毕竟在今天之前,齐家上上下下都以为嫁进来的不是我,是我的姐姐。
我那性温良恭俭让,易心软好说话,关照他人、体恤奴仆到名声在外的姐姐。
而不是我这样的货色。
祠堂内昏暗无比,寒风顺着门窗的缝隙吹进来,吹的我浑身冰凉。
突然之间,齐稻的身体就像风中的稻穗一般,微微晃动了几下后,突然径直朝我猛扑过来!
丑陋的脸孔仿佛在对我狞笑。
电光火石间,我不合时宜地想,这么沉重的东西,到底是如何摇动的?
也许是过度惊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没有发出哪怕一丁点声音。
我迅速从那块湿漉漉、黏糊糊的破旧垫子上爬起身来。与此同时,我紧紧握住手中的烛台,毫不犹豫地朝着齐稻的咽喉部位狠狠刺去!
一下,两下……
齐稻终于不动了,直直地立在祠堂正中。
我这才如梦初醒般地意识到,自己的脸颊上传来一阵阵温热。我战战兢兢地伸出手去触摸,手指所及之处竟是湿漉漉、黏糊糊的液体——那分明就是鲜血!
定睛一看,只见那个用稻草扎成的人形正源源不断地渗出鲜红色的血液。
血水顺着稻草人的身体流淌下来,滴落在地上形成一滩猩红的血泊,飞溅的血迹沾染上我的嫁衣,让我的喜服更加鲜红。
血腥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刺激着我的鼻腔和喉咙,让我几欲作呕,又想失声痛哭。
我脱力地瘫倒在簸箕上,破旧的垫子被我的动作带动翻倒,只见垫子的背面,还有着洗不净的深褐脏污,甚至有了霉点。
齐稻身上昂贵奢华的布料在窗外零星的月光下反射着莹莹的光。
3.
我原以为老夫人说自己身体不适是托词,但我入府的第二天,她便真的卧床不起。
清早,我一出房门,便看到齐彬正焦急地在廊下踱步。
看到脚步匆匆的郎中,齐彬忙问「老夫人怎么样了?」
郎中一时语塞,好半天才开口:「贺喜少爷少奶奶,是老夫人有喜了,已近临盆,只是老夫人月事早无,是昨夜睡梦深重,今早下身见了血,这才发现有孕……」
这回轮到齐彬无言以对,脸上表情变幻莫测,「真是意想不到啊,我父亲六十有余,母亲也已经年过半百……他们还真是情深意浓。」
郎中哆哆嗦嗦地跪着,瞄了我一眼,随口恭维着,「这也是齐家老爷龙精虎猛,齐家既得贵子,又得家神认可的新妇,双喜临门。」
我冲着郎中轻轻地点了点头。
虽然齐彬不肯碰我,但好在机缘巧合,一切终于按照计划展开了。
「恭喜相公。」我收敛表情,走到齐彬的身边,轻轻挽上他的胳膊,「老夫人有孕,齐家能开枝散叶这是好事,相公为何愁眉不展?」
齐彬拍了拍我,语气难得的和善,「母亲再度有孕;齐家到我这代终于有个女人能过了考验,看来齐家日后必定蒸蒸日上。」
我应和地笑着,自知作弊,昨夜的惊魂却挥之不去。
昨晚,祠堂里血污满地,齐稻如同鬼魅一般直直立在我的面前。
我虽心焦如火,但仍按捺下情绪,没有大吵大闹,甚至没有通传下人。
我不发一言地擦净脸上的血,又用装点祠堂的绸布将地上的血迹擦拭干净,把脏污了的红绸塞进衣冠济济的齐稻身体,又把血污得厉害的稻草抽出,扔进祠堂里的火盆,剩下弄乱的稻草细心归置,直到不细看看不出问题。
我这才打开窗子,散去屋内浓重的血气。
屋外的守卫依然未归,我重新跪回齐稻身前,假装无事发生。
齐稻是家神,亦是家主。
我必须要得到齐家家神的认可,如果他不认可,我只能不让别人发现。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成为齐家夫人。
我平日惫懒贪玩,少有的这般洒扫庭除。如此贤德倒真是有几分像姐姐了。
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姐姐的脸,姐姐握着我的手,一副推心置腹的架势,「齐彬的母亲是二姨娘,齐彬的奶奶也是二姨娘,齐家的正妻总是早早去世,如你实在有意齐家,便不要在意名分,嫁做姨娘。姐姐做正妻主母,自然也不会亏待你。」
见我垂头不答,姐姐叹了口气,「你从小自由惯了,干嘛要进深宅大院操持一家老小呢?」
「那你为什么非要嫁齐彬?你忘了你以前怎么说的吗?」我问。
姐姐沉默了会,也许是不想说些自己和齐彬情投意合之类的话刺激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这……不是都定好了吗?」
4
齐家的长子要和姚家的长女联姻,这是在我们出生前就定好的。
我与姐姐是同父同母的双胞姐妹,出生时头尾相接,似双珠璧合,这般同时降生,如何分清长幼?
于是满月宴上,我和姐姐同时被各自的乳母抱着,由父亲决断。
乳母在我和姐姐的背后拍打一下,我呛咳不已,哭出声来,姐姐则被稳稳地抱着,被打了也不哭,只是柔柔地看着父亲笑。
于是她便成了长女。
能嫁给齐彬的长女。
作为次女,不必作为大家闺秀培养,我从小便女扮男装去私塾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