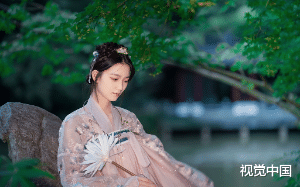1
第五日,榻上人依然未醒。
倾荷和前些天一样为这人脱下衣裳,揭开层层包裹的布条。
伤口很深,布条取下时还挂着粘稠深红的血迹。她小心翼翼清理好伤口,撒上药粉,再重新包扎齐整。
再看床上那张苍白没有血色的脸,她眼里忧愁更甚。
老爷子生前在江上打渔为生,时常带倾荷一起,家中不算富裕,但爷孙俩自得其乐,不觉悲苦。
原本平静的生活在年前被打破。
那阵子雨水多,老爷子年事已高,染风寒后一病不起,没挺多久便撒手人寰。
他留给倾荷的只余江边这间茅草屋,还有艘小小的渔舟,从这以后,她一直独居在此。
事情还要从五日前的午后说起。
她撑着船到江上,鱼没捞到几条不说,瓢泼大雨说来便来,打得她措手不及。
她慌忙往回赶,回城路上在江岸边的浅滩暼见一团黑影,好奇心驱使,她划桨过去欲瞧清那团黑影究竟所谓何物。
岸边变了颜色,绿水变红水,倾荷心怦怦直跳,下船慢慢靠近。
她伸手一推,那团黑影露了真容。
原是个人,对方双目紧闭,衣衫褴褛,满身血污,腰腹与手臂还在淌血。
探过鼻息,人还活着,倾荷犹豫片刻,终是将人拖上船带回家中。
这人身量高,往榻上一放便占去大半。倾荷没多少地方可躺,在地上将就几晚后,她只希望对方赶紧醒来。
盼着盼着,倾荷将人盼醒。
一阵咳嗽声自屋内传来,倾荷还没走到床前,救下的人已坐在床沿。
对方身形摇晃,目光却定定锁住她,十足防备。
倾荷笑容僵住,看到对方的眼神后低下头,闷声道:“你醒了。”
盛安没应声,转而四下打量,完全陌生的景,以及完全陌生的人。
眼前人少年模样,身着粗布衣裳,身形单薄,长发随意束在脑后,视线飘忽不定。
盛安蹙眉,哑着嗓子询问倾荷:“这是何处?”
“这是我家。”
这是她的地盘,何况自己还是对方的救命恩人,有什么好怕的。想到这儿,倾荷昂首挺胸,底气也多出几分。
只这暗想的功夫,闪着寒芒的剑锋已抵在她喉间。
“说,你是谁,带我到此处有何目的。”
这把剑落在浅滩上,离盛安不远,倾荷默认属于他,一并捡了回来。
现在剑被他握在手里,欲取自己性命,倾荷又惊又怕,颤着后退两步。
她退,剑也长眼似地不离她喉间半分。
惊惧褪去,她心生怒意,气着气着又觉委屈,泪已在眼眶打转。
“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救了你,你便这么对自己的救命恩人。”
“谁知你是真心救我,还是另有所图。”盛安收起剑,对她的话仍不能全信。
“一个半死不活的人,我能图你什么。”
“你完全可以将我丢在那里,自生自灭。”
“我救的你,你不谢也就罢了,嘴巴还这样坏。”
盛安听她孩子气的口吻,放下剑,嘴角似笑非笑:“那你说,你如何救的我。”
倾荷闻言从遇到盛安开始说起,包括如何带他回来,如何照料等等。
当然,倾荷的确存了别的小心思。她刻意将其隐去,断然不能说出口,否则以这人的脾气,八成又要对自己拔剑相向。
“小兄弟年方几何?”盛安问道。
“啊?”倾荷被这没头没尾的话弄得有些懵,反应过来后摸了摸鼻子,老实回答,“立夏过完便十七了。”
“可有姓名。”
倾荷迟疑片刻,应声道:“他们都叫我小河。”
“好,在下谢过河弟救命之恩,方才多有得罪,还请河弟莫怪。”
听得一个谢字,倾荷喜笑颜开,可隐约总感觉哪里不对,想破脑袋也没能想出来。
盛安重新躺好,合上双眼,倾荷记着他该喝药,去棚子里生火熬药。
等药熬好,她后知后觉被盛安占了便宜,盛安一口一个河弟,却不说自己名姓和年纪。
倾荷端着药放到床边,打算向盛安问个明白,可盛安似乎睡着了。
看在盛安伤重的份上,倾荷没叫醒他,决定下次再同他计较。
2
因着伤势,盛安清醒的时候不多,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任由倾荷摆弄。
药苦,浓烈的味道直冲天灵盖,倾荷熬的时候不仅要被烟呛,还要被药呛。
她在棚子里咳嗽连天,熬完药时免不了对盛安生出几分埋怨。
碗中黑色汁水微微晃动,倾荷捧起熬好的药,吸紧鼻子,脚下走得慢吞吞。
到床前时,药没有洒掉一滴。倾荷松了口气,坐在床沿,扶起盛安靠在自己肩膀,将药送到他唇边。
盛安碰了碗便双眉紧蹙,可仍张着嘴,到底是把这碗药喝得底朝天。
常言道良药苦口,倾荷小时候生病不爱喝药,老爷子塞块蜜饯才肯乖乖喝掉。
一包蜜饯要不少钱,药亦如此,打那后她便尽力不让自己生病,或者生病后喝药喝得快些。
所幸盛安从没叫苦,不论倾荷喂药还是喂吃食,都极为配合。
等药喝完,倾荷准备出去时,盛安眼神清明,自行挪动身体倚靠在床头。
“你受累了。”
冷不丁一句话,倾荷起身的动作顿住,侧过脸去看盛安,只一眼又耷拉下脑袋:“算不上累。”
盛安莞尔,苍白面庞现出一丝生机。他原本同样苍白的唇,此时沾着薄薄水迹,纹路已被润泽,开合间,连那苦涩的药汁似乎也变得香甜。
“在下占了位置于心有愧。”
“等你走后我便有位置了。”倾荷拉回思绪,收回眼角落在他唇上的余光。
“若你不介意,你我二人同榻而眠,这样总归舒服些,只消这床分我少一些便可。”
地上不太平整,江边湿气又重,倾荷每日起来少不了一身酸痛。
这份提议说不心动是假的,可盛安日日枕着那把剑睡,况且她虽女扮男装,到底还是男女有别。
“不差这一日两日。”
倾荷丢下这句话,忙不迭往外走。
这天用过午饭,她坐在院子里劈柴火,没过多久,肚子不受控制地叫出声。
盛安有伤在身,吃不了油腻荤腥,倾荷嫌麻烦,吃食便也不分。
劈柴火是用劲的活,她跟着这么吃自然饿得快,人没力气,索性丢掉斧头等着吃晚饭。
待天色变暗,她煮上一锅白粥,再炒了挖来的野菜,先喂盛安吃完,再回到桌前狼吞虎咽。
入夜,难题又摆在她眼前。
天公不作美,倾荷刚吹灭蜡烛,雷雨接踵而至。潮气从四面八方钻进屋里,她身上裹着的衣裳很快和皮肤黏在一块。
她翻来覆去,盛安绕是再累,听她弄出的声响也没了睡意。
盛安试探问道:“怕?”
倾荷不动了。是怕,这几天除去地上不舒服,还有一个原因便是担惊受怕,盛安会使剑,难保半夜趁她不注意痛下杀手。
“你救了我,我欠你一条命,断不会伤你。”
“真的?”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那你记着说话算话,先……先把剑拿开。”
这段时日盛安能不动便不动,好叫伤口快些愈合,那天拔剑对着倾荷已是痛苦非常,再抬手摸剑恐又会撕裂伤口。
“在下行动不便,恩公姑且信我一回。”
倾荷将信将疑,又是一声惊雷,雨势渐猛,她没再犹豫,麻利脱鞋上床躺好。
枕上被上都染了药味,闻着却不苦,倾荷脱掉受潮的衣物钻进被窝,只一颗脑袋露在外头。
盛安周身暖和,不似头晚那般,烫得倾荷以为会烧成傻子。
倾荷打算等盛安先睡,自己再睡,结果没多久便眼皮打架,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盛安艰难翻身,同倾荷面对面。眼前这名乡野男子似乎并无威胁,样貌年轻,人事当是经历不多,平日过得粗糙了些,五官细看倒也称得上标致。
此前他同仇家交手,身受重伤,漫无目的地逃离,只顾甩脱追杀。
逃至江边时,想着或许天要亡他,他再无力气,眼前一黑朝前坠去。
万幸自己命不该绝,劫后余生,盛安心中一时五味杂陈。
从谷中出走漂泊至今,满打满算已有三年之久,他竟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
山谷名为栖风,这些年几度易主。他听闻消息,了然那里已无自己容身之处,再无回去必要。
叨扰倾荷已是板上钉钉,倒不如借此机会好好休整一番,待日后身体痊愈再做打算。
这样想着,疲惫和着困意,他也沉沉睡去。
3
榻上总归是比地上舒服许多,倾荷本还战战兢兢,一夜过后相安无事,胆子便大起来。
那把剑盛安不让碰,倾荷有次睡着,手无意识碰到剑鞘便被他毫不客气地甩开。
力道之大,倾荷顿时清醒,手上火辣辣的疼。
盛安冷冷告诫她,未经允许不得随意乱动他人物件,她咬牙没吭声,只默默在被窝里揉着被打疼的手。
这救命恩人当得窝囊,倾荷后悔真不该一时头昏救下盛安。无奈她连三脚猫的功夫也不会,即使病体,盛安也比她强上太多,当其对手显然她还不够格。
盛安察觉倾荷比之前更怕自己,伤好些后,倾荷不再给他喂饭喂药,端进来即放即走,一只手总是背在身后。
再睡觉时,倾荷一上床便爬到角落里,缩到紧贴墙根,背对盛安。
绕是再迟钝,盛安也反应过来,许是之前下手太狠,又把她吓着了。
倾荷见盛安如见瘟神,白天能避则避,只有为盛安擦身更换衣物时,她会待得久些。
今日天热,屋里有些闷,盛安只躺着也出了不少汗,浑身黏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