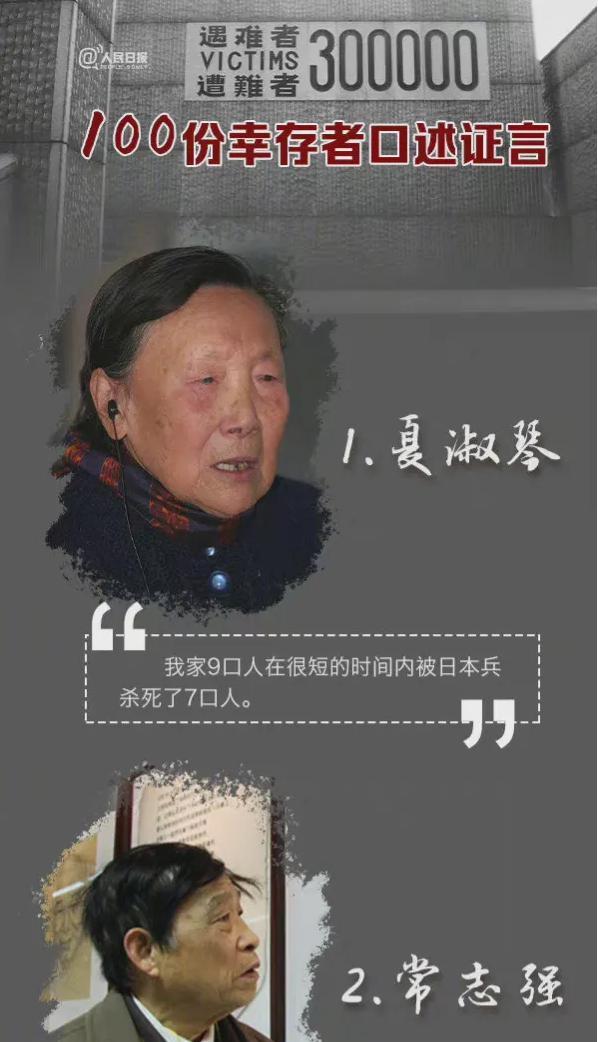“妈,你给我端一碗糖水来吃,我疼死了。”这是陈得寿的姑母留在世界上最后的一句话。在1937年南京那场浩劫里,当时的他还不到6岁,但回忆起往事,他说:“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天发生的事。” "妈,你给我端一碗糖水来吃,我疼死了。" 这是陈德寿姑母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2016年,年近八旬的陈德寿坐在察哈尔路的家中,向前来采访的人讲述着七十多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他的声音很平静,却藏着无法抹去的伤痛。 "那是1937年12月13日,我虚岁六岁。"陈德寿回忆道,他出生于1932年10月,那时家住在南京三山街附近的天青街古钵巷四号,在一座三进的院落里。在战争来临前,他们家过着还算安稳的小康生活。爷爷陈金波在中华门开了一家估衣店,父亲则开了一家服装店专做制服,家里有四部缝纫机,还请了师傅和徒弟。 日军进城那天,他们放火烧了天青街街头的房子。陈德寿的父亲和街坊邻居出去救火,结果被日本兵一起抓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一天早上九十点钟,一个日本兵拎着箱子来到他们家,挨家挨户地搜查。 "爷爷看到了日本兵,不想得罪他,就把香烟糖果拿出来请他吃。"陈德寿说,"但鬼子根本不要这些,他要花姑娘。" 当时陈德寿的母亲怀着身孕,姑母陈宝珠一手抱着小表妹,一手牵着小表弟。日本兵一看见姑母就拖着她从第三进拉到第二进。姑母将表妹交给奶奶后与日本兵周旋,但日本兵不耐烦了,拔出刺刀对着姑母的大腿深戳一刀,姑母痛得蹲下来。日本兵又在她身上连戳五刀,总共六刀,然后转身就走。 "姑母疼得难受,对奶奶说:'妈,你给我端一碗糖水来吃,我疼死了。'"陈德寿回忆道,"奶奶跑回家里把糖水端过来时,姑母已经断气了,流血太多,被刺到了要害。" 就在姑母被日本兵杀害的那天晚上,陈德寿的母亲生下了一个女婴——他的妹妹。但日本兵的骚扰仍在继续,他们不断地来抢东西,寻找"花姑娘"。母亲只能将生孩子留下的带血纸张放在地上,有的日本兵看到后会离开,有的则会掀开被单查看是否真的生了孩子。 熬过了六天后,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兵。陈德寿的爷爷向他诉说家里的遭遇,这个日本兵说:"我是当兵的,家里也是开店做生意的,是征兵征来的。"他带着爷爷找到了棺材店,为姑母买了口棺材,还帮忙找来了粮食和小菜。 "你爸死了。"这句话是在南京大屠杀后一个多月才由爷爷告诉陈德寿母亲的。那时日本人已经建立了维持会,发出通告称不再杀人,当地秩序开始逐渐恢复,他们一家从难民区回到了家中。 一个皮匠告诉了陈德寿爷爷关于父亲死亡的详情。原来,当天被抓的人中,日军审问他们是否愿意跟着日本人走。陈德寿的父亲坦诚地说自己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妻子还怀着孕要临产,恳求能回家。结果第二天早上,日军把他和另外两个表达类似意愿的人拉到了承恩寺门口,当场枪杀,还用刺刀戳了两刀。 "四十天后,爷爷和舅舅一起去收尸,"陈德寿回忆道,"收尸时父亲的伤口还在流血。过去有种说法,人死后见到亲人伤口才会流血。"父亲的尸体被埋在了舅舅家旁边,与此同时,姑母的遗体也被舅舅和几个人一起抬到邓府山埋葬。 失去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陈家从此陷入了贫困。爷爷只能把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变卖度日,包括四部缝纫机和所有的布料材料。母亲则在邻居的介绍下帮别人喂奶赚钱,以至于自己的女儿——陈德寿的妹妹——吃不饱,身体一直不太好。 1940年,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一种痢疾在日本控制区传播,感染后不能吃东西,一吃就吐。陈德寿年仅三岁的妹妹首先感染,因为没钱医治,很快就去世了。不久后,奶奶也感染了同样的疾病离开人世。 "家里穷得揭底了,"陈德寿说,"邻居劝我妈改嫁。"他们住在第三进,前面有一家姓李的锤金箔人家,有个未娶妻的老伯帮忙埋葬了奶奶和妹妹。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陈德寿的母亲被迫改嫁了,留下爷爷和三个孩子:陈德寿、表弟和表妹。 爷爷将七岁的表弟送到了孤儿院,表妹则被送去做养女。但悲剧并未就此结束,表弟在孤儿院被告知病死了,表妹后来也没能活下来。一个原本热闹的大家庭,最终只剩下陈德寿和将近七十岁的爷爷相依为命。 "爷爷还要做裁缝,帮人家缝缝补补,"陈德寿说,"弄两个钱回家维持生活,有时候不够还要跟我妈要,所以日子是不好过的。" 熬到陈德寿十四岁时,也就是1946年抗日战争刚结束,他跟随家族传统出去做了裁缝学徒。1948年,继父和母亲生了个弟弟,但仅仅八个月后,继父因旧伤复发去世。爷爷被送进了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老人堂,母亲靠帮人洗衣服维持生活,有时候别人会给些米让他们果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