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将率领勇士登上钓鱼岛,破坏日本的灯塔,插上五星红旗!”1996年,陈毓祥语气铿锵地对记者说道,结果如何? 1996年9月26日,钓鱼岛附近的海水冰冷刺骨,陈毓祥却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他的身影瞬间被浪花吞没,而这一跳,也让他的名字刻进了历史。那天的海面并不平静,狂风卷着巨浪拍打着“保钓号”的船身,船上的十七名勇士屏住呼吸,目光紧锁在不远处那片隐约可见的岛屿上。 他们此行的目标很简单——登上钓鱼岛,拆掉日本右翼分子竖起的灯塔,把五星红旗插上那片属于中国的土地。可这简单的目标背后,藏着多少凶险,谁也不知道。 四天前,9月22日下午,香港码头挤满了人。渔船的汽笛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味和人群的喧嚣。陈毓祥站在“保钓号”船头,身穿橙色救生衣,脸上带着一丝笑意。他回头望了眼送行的群众,心里清楚,这一趟不是普通的出海。 他低声对身旁的船员说:“无论如何,我们得让日本人知道,钓鱼岛不是他们的。”话音刚落,货轮的马达轰鸣起来,缓缓驶向茫茫东海。 陈毓祥不是莽撞的人。他出生在广东潮阳,8岁随父母移居香港,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聪慧。北角堡垒山官立小学的课桌上,他总是埋头苦读;英皇书院的操场上,他跑得比谁都快。后来,他考进香港大学,拿下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又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了硕士。 毕业后,他做过老师、当过电台评论员,甚至爬到电视台副总监的位置。1985年,他还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前途一片光明。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才子,为何会站在风浪肆虐的船头,赌上性命去保卫一个遥远的岛屿? 答案藏在他心底那句无声的信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早在1970年代,他就投身保钓运动,那时他还是个学生,站在维多利亚公园挥舞标语,喊得嗓子都哑了。1996年,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纳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还派舰艇巡逻,日本右翼分子更是在岛上建起灯塔。这一切,像一把火点燃了陈毓祥心中的怒气。 他找到记者,语气铿锵地说:“我要带人登岛,把他们的灯塔拆了,把五星红旗插上去。”记者问他怕不怕,他笑笑:“怕什么?这是中国人的地盘。” “保钓号”出海后,麻烦接踵而至。日本早有准备,飞机低空盘旋,军舰步步紧逼,三艘原本要接应的台湾渔船被十六艘日舰围困,只能无奈返航。陈毓祥站在甲板上,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眯着眼看向远方,低声骂了句:“日本人真是不要脸。” 船长魏立志劝他小心,可他只是拍拍对方的肩膀:“我们不往前冲,谁来守这片海?” 经过四天颠簸,“保钓号”终于在9月26日清晨闯进钓鱼岛1.5海里的海域。眼前的岛屿近在咫尺,可风浪却越来越大,小皮艇根本没法下水。陈毓祥皱着眉,盯着那座灯塔若隐若现的身影,心里一阵不甘。他转头对五名队员说:“我们游过去。”没人反对,大家迅速套上救生衣,用绳索绑住腰。陈毓祥第一个站到船边,海水拍在脸上,冷得刺骨。 他深吸一口气,纵身跳下。 那一刻,海面像张开了巨口。陈毓祥刚入水,脚就被绳索缠住,他挣扎着想解开,可一个浪头打来,他的头狠狠撞上了船舷。队友眼睁睁看着他被卷进水里,喊声被风浪吞没。另一名队员方裕源也被巨浪拍晕,幸好被救起送往医院。 而陈毓祥,等被捞回船上时,脸色已经发白,嘴角淌着泡沫,气息全无。船员们围着他,手忙脚乱地按压胸口,可无论怎么努力,他都没再睁开眼。那天下午1点,这位45岁的勇士永远闭上了眼睛。 消息传回香港,整个城市陷入了沉默。9月29日,维多利亚公园挤满了人,5万支烛光在夜风中摇曳,有人低声啜泣,有人紧握拳头。他的妻子刘舜卿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站在人群中央,泪水模糊了视线。新华社香港分社送来一面五星红旗,盖在他冰冷的遗体上,像是在诉说他的未竟之志。 一个星期后,100多名港台勇士再次出海,三人成功登岛,在钓鱼岛上插上两岸旗帜。那一刻,陈毓祥的牺牲仿佛有了回响。 陈毓祥走了,留下老母亲、妻子和一双儿女。他的家在香港,钓鱼岛的风浪从没吹进过那个温暖的小屋。可他选择用生命告诉所有人,这片海,这座岛,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守护。 20多年过去了,他的故事依然在民间流传,提醒着我们:爱国不是口号,而是有人用血肉铺成的路。 陈毓祥倒下的地方,海浪依旧翻滚。那片他用生命捍卫的土地,如今仍是中国人心中的痛与念。他的名字,刻在历史里,也刻在每一个不曾忘记的灵魂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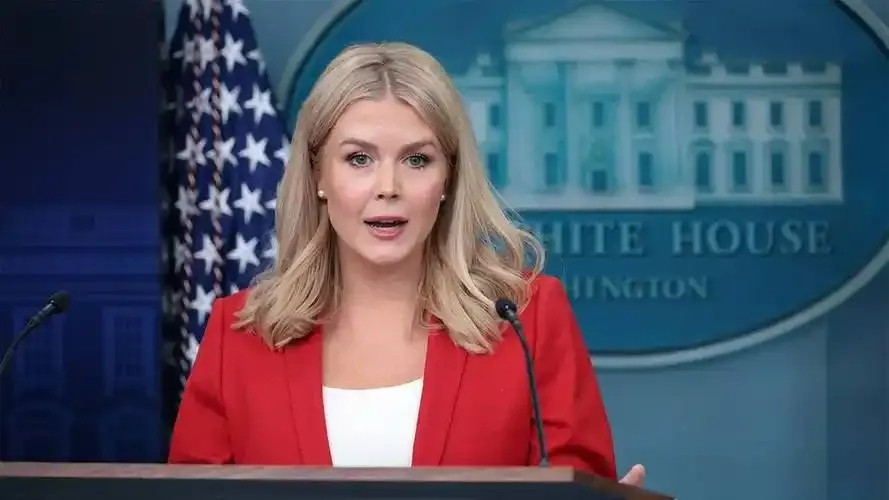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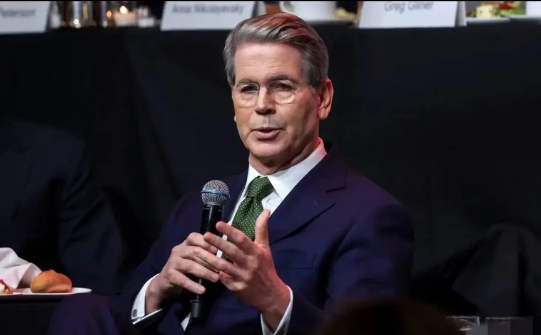



用户10xxx03
勇士的后代应给予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