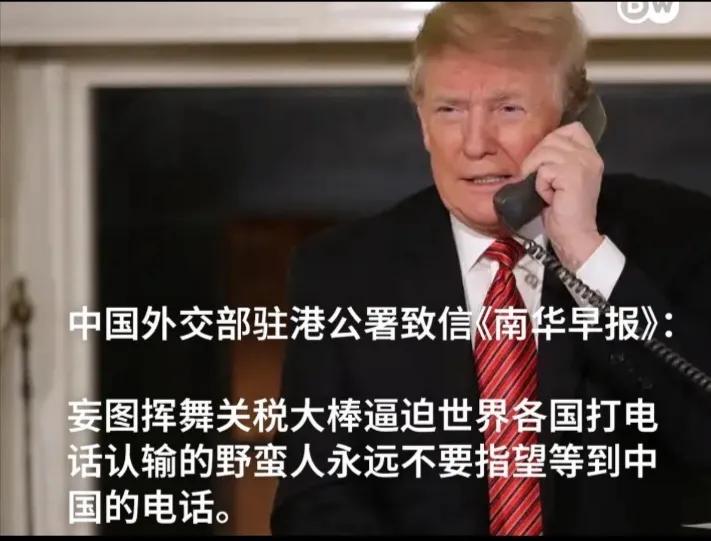1965年,一次培训时,训导员玛格丽特架不住海豚的多次纠缠,和它发生了性关系,不久玛格丽特离开,海豚见状竟以死明志! 夕阳洒在维京群岛的海面上,玛格丽特坐在浸水屋的甲板边,海豚彼得突然跃出水面,溅起一片水花,她笑了,却不知这笑背后藏着多少秘密。1965年的圣托马斯岛,空气里混杂着海盐和椰树的味道,木屋的地板被水浸得发软,录音机放在一旁,断续播放着“hello”的音节。 23岁的玛格丽特穿着简单的衬衫,头发被海风吹得凌乱,她低头记笔记,彼得却在水里翻了个身,发出清脆的哨音,像在喊她。她抬头,眼神里闪过一丝疑惑:这只海豚,是不是懂了什么她没说出口的事? 那年,玛格丽特刚从英国来到这座小岛,受雇于神经科学家约翰·礼博士,参与一项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实验——教海豚说英语。NASA掏了钱,理由很玄乎:如果人类能跟海豚聊上几句,没准哪天也能跟外星人搭上话。 玛格丽特不是科学家,只是个爱动物的年轻人,觉得能跟海豚一起工作简直像做梦。她被安排住进一栋特制的房子,屋里全是浅浅的海水,床和桌子漂在木板上,彼得和另外两只海豚就在水里游来游去,像她的室友。 最初的日子像冒险。每天清晨,玛格丽特穿着泳装,泡在水里,手里拿着鱼干,教彼得模仿她的发音。“Hello,Peter!”她喊,彼得歪着头,嘴里冒出咕噜声,像个学舌的幼儿。 她会拍手笑,彼得就跃出水面,甩尾巴溅她一身水。同事们说,彼得聪明得吓人,脑子比狗还灵,记单词快得像在炫技。几周下来,彼得学会了“ball”“play”几个词,甚至在她说“work”时,顽皮地回一句“play”,然后在水里打滚。 玛格丽特记在笔记本上:*彼得表现出理解力,可能有情绪表达。* 她觉得,自己离奇迹不远了。 但奇迹没来,麻烦却来了。实验进行到第二个月,彼得变了。它不再专心听她说话,训练时总心不在焉,喜欢凑过来用鼻尖蹭她的腿,眼睛亮晶晶的,像在讨好。玛格丽特起初没多想,海豚爱玩,她也常跟彼得一起游几圈,扔个球逗它开心。 可彼得的动作越来越大胆,有时会轻轻咬她的脚踝,或者用身体贴着她转圈,尾巴拍水拍得哗哗响。一次,她坐在甲板上接电话,彼得突然冲过来,撞得木板晃了晃,发出一串急促的叫声,像在抗议她分心。 玛格丽特愣住了,心跳得有点快——这不是玩闹,彼得在乎她,在乎得有点过头。 她把这事告诉了约翰博士。博士推了推眼镜,笑着说:“公海豚,六岁,正闹腾的时候,别放心上。”但玛格丽特放不下来。她开始留意彼得的眼神,那里面有种她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像依赖,像渴望。她试着减少亲密接触,专心教单词,可彼得不干了。 它会故意游开,撞墙,或者沉在水底不理她,像个赌气的小孩。实验数据停滞,玛格丽特急得睡不着,屋外海浪一声接一声,像在催她做决定。 那天晚上,月光从木屋的窗户漏进来,水面泛着银光。彼得游到她身边,鼻尖轻轻碰她的手,发出低低的呜咽。玛格丽特看着它,心软了。她把手伸进水里,试着安抚它,像哄孩子一样。彼得安静下来,贴着她,身体微微颤抖。 她后来回忆,那一刻她没多想,只觉得彼得需要她,就像她也需要这份联结。接下来的事,她没细说,只承认自己“帮”了彼得一把,让它平静下来,继续实验。没人知道细节,屋里只有海水拍岸的声音,和彼得满足的哨音。 这事像颗埋下的种子,悄悄生根。玛格丽特和彼得的相处更亲近了,它的情绪稳定了些,训练也恢复了点进展。但岛外的世界不平静。1960年代,美国街头喊着自由与反叛,性解放的口号让人们既兴奋又不安。 实验的消息不知怎么漏了出去,报纸开始捕风捉影,写什么“女人与海豚的怪事”。有人说这是科学,有人骂这是堕落。动物福利的呼声也冒了出来,指责实验让海豚受苦。NASA坐不住了,1966年,实验被叫停,理由是“没成果,预算超支”。 最后彼得被送到了迈阿密的实验室,条件远不如岛上。几周后,消息传来:彼得死了。它沉到水底,停了呼吸。海豚得主动换气,停下来就等于放弃生命。约翰博士说,它是想家了,想她了。 玛格丽特听到这消息,坐在伦敦的公寓里,盯着窗外的雨,半天没说话。她后来说,彼得不是宠物,也不是实验品,它是朋友,是她生命里独一无二的存在。2014年,BBC拍了纪录片《与海豚交谈》,她第一次公开讲了这段往事,语气平静,眼里却有泪光。她没提爱,只说:“我尽力了,但也许我们都错了。” 海浪依旧拍打着维京群岛的岸边,木屋早已不在。彼得的故事沉入海底,玛格丽特的回忆却像潮汐,时而浮现。她和彼得的十年相遇,像一面镜子,照出人类对未知的渴望,也照出我们对生命的亏欠。 1966年后,美国动物福利法开始收紧,实验动物的保护多了几分约束。今天,科学家们仍在研究海豚的语言,但没人再敢把它们关进水屋。或许,真正的交流,从学会尊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