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大上学,在北大求学,将近70年过去了。种种往事,清晰如在昨天。前一段写了一篇《燕园琐忆》发到朋友圈,但仍觉得“忆”犹未尽,回味不尽。所以,续写这篇再忆。

《此世今生未名情》
记得是1956年8月下旬,我们在福建教育厅的组织下去北京上大学。当时福州去北京上大学的人数有五六十人,光我们师大附中考上北大、清华就各七人,还有北航、北石、北农大的六人。
当时福州到上海没有铁路,我们坐小轮船到南平。南平到上海的铁路刚建好,客运还没有正式通车。我们只能坐运货的火车,没有座位,只能在车厢内席地而坐。火车没有行车时间表,说开就开,说停就停。
一天中午车到鹰潭,大家下车找饭馆吃饭,我们吃面条,交了钱,面还没端上来,突然有人喊“开车了”,大家也顾不上吃面,飞奔回火车上。结果,上车半个多小时,仍未开车。有的同学猜想那一声可能是老板叫人喊的。
坐货车到了上海,就换成客车,我们一行顺利到了北京。火车站飘扬着各个大学色彩缤纷的旗帜,我想北大的校旗一定很醒目,可是找了半天,好容易才看到一辆卡车,上面有一面北京大学的小旗,很不显眼。上卡车,到北大已经晚上九点了。由于旅途疲劳,我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一早被刘烈茂揪醒。
我的燕园九年的难忘岁月,就是从那个早晨正式开始的。
一

由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外国贵宾多来北大演讲,国家领导人和各部委负责人都来校作报告。周总理的报告高瞻远瞩,纵论天下事,政治家、外交家的风采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给我印象很深的报告还有1957年“反右”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来北大作报告说:“我们是引蛇出洞,是个阳谋,不是阴谋”,说完哈哈大笑,声震报告会场。
胡耀邦(时任团中央书记)作报告,在台上来回走动,动作幅度大,表情丰富,很有激情,讲到出国参加国际青年大会时,他说,“我讲完话,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我身高不到七尺,其貌不扬,为什么他们这么尊重,因为我背后有强大的国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
陈伯达(时任《红旗》主编)1958年7月1日在北大演讲,浓重的福建闽南话口音,我听了都非常吃力,其他省的同学更是听不懂了。
陈毅(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高校毕业生作报告,直言不讳地说梅兰芳唱戏唱得好,就是为人民服务,要他学那么多马列干什么?;一个学外语的,精通外语,当好翻译,让宾主交谈水乳交融,就是为政治服务;如果业务不好,就像钝刀子切肉,宾主无法很好交流,空讲政治有什么用?陈毅的话,对刚批判过“白专道路”的我们,真是振聋发聩啊!
学术报告方面,有时有苏联、东欧等国的专家来讲学。我现在还依稀记得有一位外国专家作了有关葡萄来源的报告,讲到中文“葡萄”一词则来自于波斯语“budawa”,意为“果子”。
至于著名学者来校讲学的就更多了。文学方面就有周扬、邵荃麟、林默涵、老舍、何其芳、萧涤非、王季思、周振甫等等。

《周扬文论选》
周扬的报告既宣传当时的政治思想,又有较强的学术理论。他在报告里提出一个“时代智慧”问题,他说一个国家时代智慧会体现在某一领域。如十八、九世纪俄罗斯的时代智慧集中表现在文学方面,列夫·托尔斯泰、契柯夫、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列夫、果戈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伟大作家集中涌现;二十世纪中国时代智慧的体现就是毛泽东思想。
二

建国后,北大中文系的专业设置、课程、人员都有较大变化。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和燕京大学中国文学、新闻两系并入,下设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与编辑两个专业。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专业并入北大,成立语言专业;1958年新闻专业转至人民大学新闻系;1959年设立古典文献专业,确立了文学、文献、语言“三分天下”的专业格局 。
几个院校中文专业合并到北大,大大加强了北大中文系。如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朱德熙都是原清华大学的教师,王力、岑麒祥原是中山大学,高名凯、林焘来自燕京大学。
北大中文系名家荟萃。不过我在校时联系较多的还是大吴先生和小吴先生,他们是我研究生时的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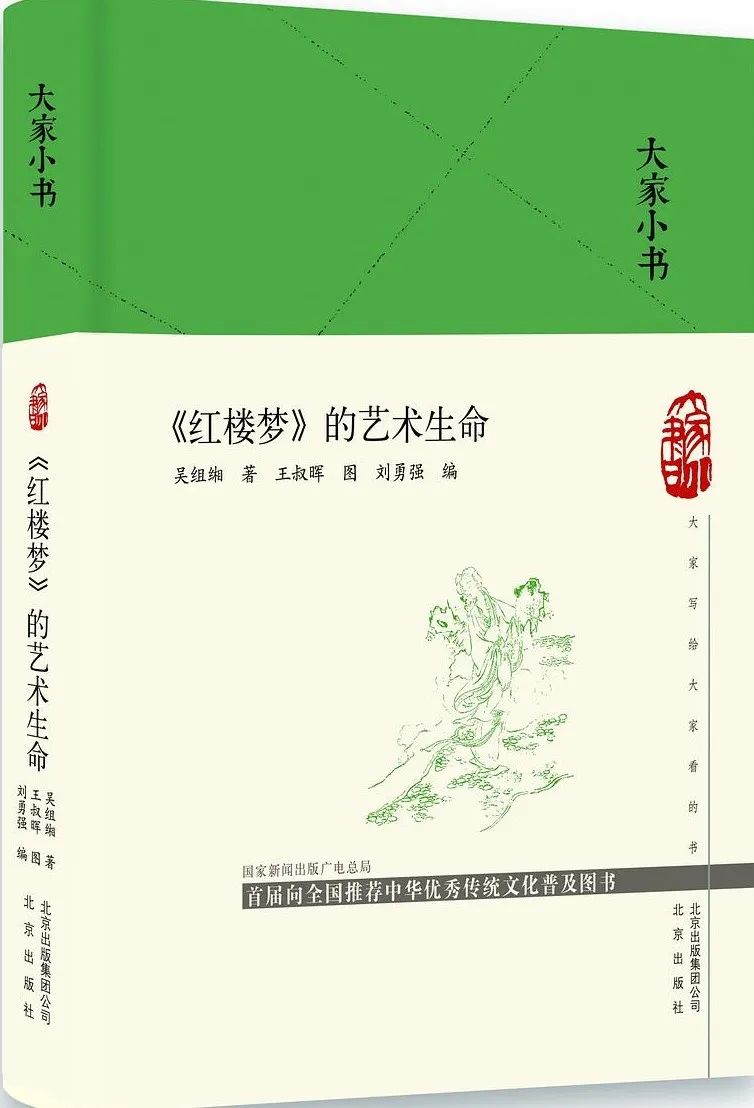
《红楼梦的艺术生命》
大吴先生就是吴组缃,他是著名红学家,与《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关系密切。按“壬午说”,曹雪芹逝世在1763年,所以1962-1963年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活动逐步展开。
这时有两件事。一件是《红楼梦》主题是“四大家族衰亡史”的提出。“把《红楼梦》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红楼梦》是四大家族的衰败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等,这些观点成为1963年以后所有红学文章的基调,成为“金科玉律”。
另一件事是1958年上海越剧院上演了越剧《红楼梦》,随后又在1962年拍成电影,都风靡全国,一片赞扬声。
但吴组缃先生坚持他的观点,认为《红楼梦》就是一个主题,写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写出了造成这个悲剧的社会根源,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社会。他不同意《红楼梦》主题是“四大家族衰亡史”、而“爱情只是掩盖”的观点,还在课堂上批评越剧《红楼梦》,认为它只表现爱情婚姻悲剧,没有表现这个悲剧的社会根源,把《红楼梦》降低到才子佳人戏的水平。

《吴组缃小说课》
大吴先生《红楼梦》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已为大家所熟知,无需赘述。可惜的是吴先生的《吴批红楼梦》没有完成,还有许多精辟见解没有得到阐发。
1993年我和刘烈茂利用在香山开古代小说研讨会的机会去看望吴先生,他说“尤三姐这个人物写得不好,因为曹雪芹不熟悉这样的人物”。对这个观点,我和刘烈茂都不太理解,一路上还在讨论。
接下来说说小吴先生。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小如先生讲课能那么精彩?除了学问渊博和讲课艺术高超这些基本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作品,特别是诗词作品的研究能将考据和欣赏结合,具有独特的体会,这当然非大学问家是做不到的。
他说:“近来我于听平伯师讲课时乃悟到考据究竟是重要的。盖如考据得不到家,欣赏的路也就容易阻梗,考据得愈精,欣赏时始愈知古人遣词设意之工巧之难。《读词偶得》便是代表此一趋向的最大证明。于是我戏名之曰‘考据的欣赏’,而以刘西渭先生的《咀华集》为‘欣赏的考据’。盖必‘欣赏的考据’才不至使人头痛,亦唯有‘考据的欣赏’才能是真正刻画入微的欣赏,如《读词偶得》所收的效果然”。
他讲的诗词都是最常见、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把考据和欣赏结合起来。如《木兰词》:“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吴先生如此解读:
此数语多为人所忽略。木兰自昨夜已见军帖,则心事重重,不言而喻,其所以停梭止织,正缘有所虑、有所忧也。何言无所思忆乎?证以《折杨柳枝歌》,知此处之“思”与“忆”,乃狭义而非泛言也。

《吴小如文集》
《折杨柳枝歌》云:“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是其所思所忆,乃男女情爱之事,所思所忆之人,乃意中之情侣恋人,非泛指一切其他人与事也。
予尝考十五国风,用“思”字者凡二十二篇,其不涉男女情爱相思义者仅七八篇耳(其中尚有是否指相思之意而不能肯定者,姑亦除外,皆在此七八篇之内)。而汉乐府及《古诗十九首》之言“所思”(如“有所思”、“所思在远道”)、“长相思”、“思君令人老”云云,皆指男女或夫妇之思;而《饮马长城窟行》之“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西洲曲》之“忆梅下西洲”,则“所忆”亦有广狭二义也。
此诗盖言木兰之所叹息,乃忧其父之年老与弟之年幼,无以充兵役,非缘己情有所钟,以婚嫁之事为念也。夫然后乃知此诗造意遣词之妙,虽本于《折杨柳枝歌》青胜于蓝矣。
又如《诗经·伐檀》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五四”以来胡适、刘大白、魏建功等权威的解释都是讽刺君子“不劳而食”。吴先生对《诗经》中“君子”一词究竟有无讽刺涵义,就有意识地进行过调查研究。而调查研究的结果,不仅《诗经》中所有用“君子”的地方,这个词不含贬义;甚至在先秦古籍,其中所有用“君子”的地方也不含贬义。这样他就自然而然得出一条结论:《诗·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两句,一定不是诗人在讽刺统治者(或剥削者),而是在他理想中希望有个不素餐的统治者,“君子”在诗中属“正面人物”。

《吴小如戏曲文集全编》
小吴先生对学生总是无私帮助、热情扶植。1963年春,北大中文系58级学生姜志雄发现何大伦的《重刻增补燕居笔记》里有《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全文,这是汤显祖《牡丹亭》创作的蓝本。
对于这个重要发现,吴先生很高兴,也和我们几个研究生说过,但他又是非常慎重的。为了搞清这篇话本是否就是嘉靖进士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杜丽娘记》,或者是否晚于汤显祖,他遍览了《燕居笔记》全书,稽考其他篇章中每一件史料的发生时间和每一篇文字的大致写作时间,这样得出《燕居笔记》里没有一篇涉及嘉靖十九年以后的作品,从而使《杜丽娘慕色还魂》是《牡丹亭》的蓝本之一的结论建立在非常可靠的基础上。吴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了。姜志雄的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6期上,这个结论已成学界的共识 。
回忆应该是真实的,还原历史的真实。应该说当时的师生关系是不正常,不亲密的。经过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多数教授成为惊弓之鸟。
那时还有一个很荒谬的说法:要警惕“资产阶级教授和党争夺青年”。在这样高压政治氛围里,我们和老师之间只是上课,谈谈学习方面的情况,很少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
林庚先生是闽侯人,高名凯先生是平潭人,林焘先生是长乐人,我从没有去认同乡关系。和老师,包括两位吴先生,也只谈谈学习上的问题,没有涉及当时的国家大事,北大校园里的传闻轶事,也没有问及家庭情况。后来我不在北京工作,也不能侍奉在侧。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有机会作了些微的弥补。

《西游记漫话》
三
北大不但名师荟萃,而且还有素质较高的学生群体。
刘烈茂是我到北大认识的第一位同学,也成为一生的挚友。他是潮州人,一天下大雪,我们两个南方“蛮子”,“二人手舞足蹈,大声欢呼‘下雪了,下雪了’”给北方同学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还津津乐道 。我们两个还打赤脚在未名湖边散步(我高中毕业照片上就有不少人打赤脚,包括女同学),遇到陆平校长,把我们叫住,说:“同学,这里外宾很多,你们还是把鞋穿上吧!”
烈茂是位公认的好人,热心、诚恳、坦率。他在“反右”时,认为对“右派”的批判和处理,不符合“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因而犯了“同情右派”的错误,延长预备党员的预备期,到快毕业才转正,预备党员当了五年。

《水浒中的社会与人生》
改革开放后,他首先提出《水浒传》的“忠奸斗争说”;对《聊斋志异》作了深入研究,出版了《新评聊斋志异三百篇》等著作,主持《车王府曲本》的整理工作。他原来身体很好,
1993年我们在北京香山参加古代小说研讨会,他邀我爬山,我爬不动,他却一口气登上“鬼见愁”。没有想到他在2010年就去世了,李文初给我寄来悼诗:“君卧银河花万丛,一堂呜咽挽歌中。西山此去仍飞雪,怎耐琼楼冷与空?”
彭庆生入学时,由于立下“青霄有路终须到,宇宙无名誓不休”的宏愿,躲在一间废弃的浴室里苦读而闻名,成为全校“白专”的典型,受了不少批判。但是后来在“大跃进”时,他报名参加劳动突击队,在修水库、深翻地等苦役里,以超人的毅力和体力,用一身汗水和泥巴,重塑自我,成为全校由“白专”向“红专”转变的典型。在我们大学毕业时,北大党委副书记张学书指示:“把这个典型留下来当研究生吧”,于是他就成为林庚先生的研究生。
我和庆生九年都住在一起,他的刻苦精神深深感动了我。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学术上取得突出的成绩。《陈子昂诗注》《唐五代乐舞书画诗选》《增订注释全唐诗》等著作陆续出版,特别是2015年出版的《陈子昂集校注》(上、中、下)成为最完备的陈子昂作品集。
2016年3月24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了庆生的力作《又见幽州台》,不料竟成了他的“绝笔”。
山东汉子袁良骏,基础好,又勤奋努力,在鲁迅、周作人、张爱玲、白先勇、丁玲等作家的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他文笔洒脱、犀利,不但有《独行斋独话》等杂文集,而且学术论文也极为锋利,有杂文之风,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香港《文汇报》有一篇文章这样评论他:“他当年在学术场域纵横驰骋骁勇善战,左冲右突,见招拆招,引人瞩目,……同时又是‘恶’名远扬的人”。“你那哇啦哇啦的嗓门,你那山东汉子豪爽的性格,你那不拘小节的快乐,你那得罪人的舌头,总是不计后果欠思索。”

《武侠小说指掌图》
其实,他是善良、豪爽,很重师生、朋友之情的。他要我和他一起写怀念刘烈茂的文章,后来由他执笔,发表在北大校友通讯上。
在吴小如先生去世后,他即写了深情的悼念文章,还严厉批评我没写。我给他解释,当时我正动手术。他安慰我不要紧张,其实这时他已病重,但没有告诉任何人。到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同学们都以为是讹传。
张仁健,江苏南通人,大学毕业后到山西工作,这位江南才子一辈子就扎根在北国土地上。他在1981年创办《名作欣赏》,经过十年动乱,这个刊物给读者提供最佳的精神食粮,如王瑶先生所说:“浏览《名作欣赏》如同走进王府井大街工艺美术商店,给人以高雅的美感享受。”
当时刊物很少,《名作欣赏》也给不少著名学者,或后来成名的青年才俊开辟了发表佳作的园地。

《山西古代游记选》
2016年重阳节,我们在北大聚会,纪念入学60周年。会上决定出一本纪念集子,由张仁健主编,他殚精竭虑谋划的纪念文集《此世今生未名情》,在2019年1月出版,而他却在2018年11月去世。这是他终身的遗憾,也是我们永久的悲痛。
我们这个小班还有几位英年早逝的同学。张继顺(1938-1984)发表了诗歌、戏剧作品,出版了《诗歌意境琐谈》等专著;天真活泼的“小麻雀”韩蔼丽(1937-2003)发表了《湮没》等小说,引起文坛的高度关注。他两人都是中国作协会员。朱彤(1930--1992)发表了《释“白首双星”》等论文,成为著名的红学家,《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
我们入学是120人,分4个小班,我在四班。到大三,要分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来中文系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兴趣文学,不愿去语言专业。于是系党总支动员自动报名。当时,都要表示坚决服从分配。120人都报了名,但同学们心里却忐忑不安,但愿不要抽到自己头上。
后来30位同学去语言班,虽然他们都是文学的爱好者,怕语言学,但是经过努力,何九盈、何乐士、施光亨、王绍新、刘月华等都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
正如李延祜在悼念王绍新时写的:你这位充满艺术气质的津门才女,本可以成为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然而却分配到了语言专业;你迅速转舵,让命运的风帆向远古驶去,去开发古汉语的宝藏,与古人对话,在古籍里徜徉;几十年面壁,三更灯火五更鸡,终于化蛹为蝶,成就了你这位具有艺术气质的语言学家;你的语言著作荣获以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命名的语言学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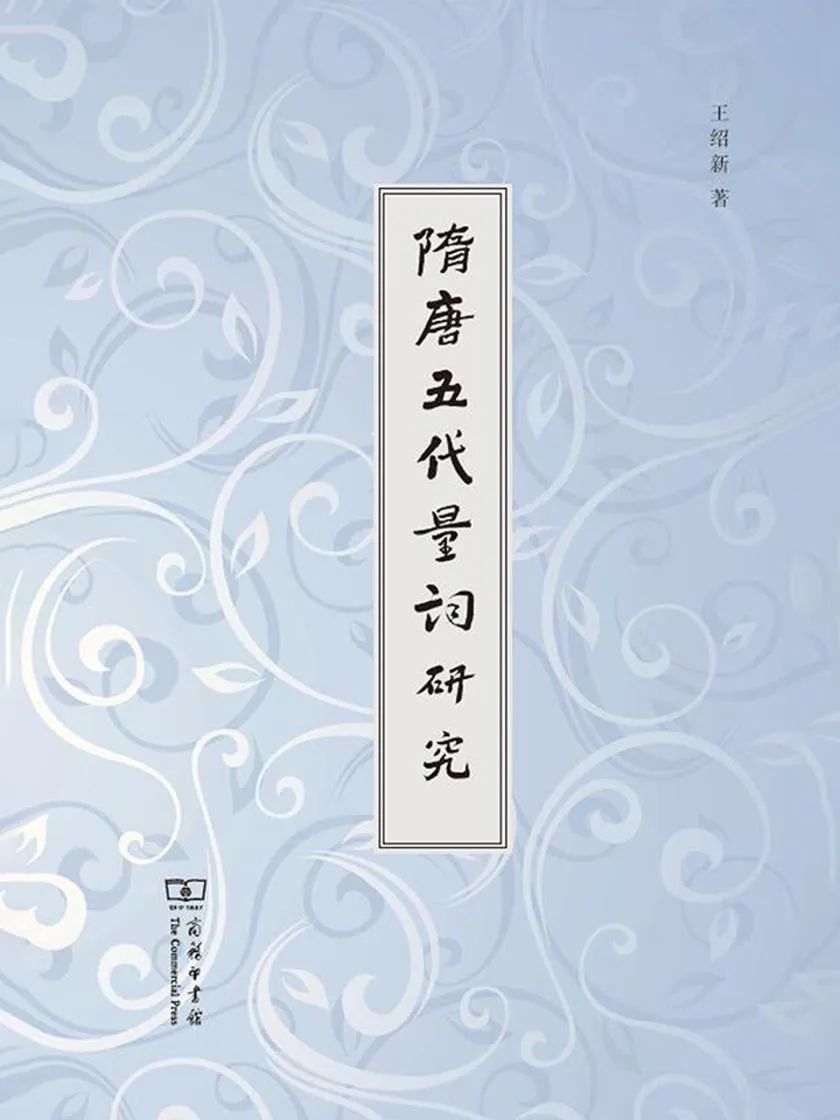
《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再说说研究生时的同学吧。从1959年开始国家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央为减轻负担,决定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北京中央机关下放到省市,从省市下放到县。到我们毕业的1961年,分配就十分困难。邓小平指示要多招研究生,储备干部。我们年级120人留了25人当研究生。
不久,周扬又说“研究生宁缺毋滥”,25人减少到9人,语言专业教授多,有7位,所以语言班30人,研究生留了5人,文学专业教授少,3个班90人,只留了4人。
先前学苏联,研究生称为副博士研究生,到后来与苏联闹僵了,而我们国家的学位制度还没有建立,所以我们就是研究生,有毕业文凭,可没有学位。我填表学历就填研究生,现在许多人不明白,老问是硕士还是博士?我回答:什么士也不是(在我这个福州人的普通话里sh,s没有区别)。

《陶渊明论略》
我们文学专业四人,分别分到文学专业仅有的四位教授名下。李文初导师是游国恩先生,彭庆生导师是林庚先生,黄侯兴导师是王瑶先生,我挂在吴组缃先生名下,因为他已经有上一届的五位研究生,我实际上导师是吴小如先生。
彭庆生大学和我同班,已经说过。李文初毕业后在暨南大学工作,他在魏晋文学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陶渊明论略》、《中国山水诗史》等重要著作在学界很有影响。2011年我到广州开会,我们在暨南大学彻夜畅谈,没想到他在2015年竟与世长辞。
黄侯兴是郭沫若研究专家,先后出版《郭沫若的文学道路》《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郭沫若文艺思想论稿》等学术专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与推重。他还担任郭沫若故居纪念馆副馆长。他是福建泉州人,归国华侨,我们当研究生的头两三年,政治氛围比较宽松,夏天我们摇着扇子,去海淀小酒店喝啤酒,学弟们戏称我们是“烟酒生”。侯兴比我大,已经90岁了,但身体还很康健。

《郭沫若与孔孟之道》
燕园生活值得回忆的事情还很多,都是我们那一代北大人的共同记忆,愿健在老同学们多写一些吧!
齐裕焜2024年10月15日于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