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谓经典?这已成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命题,在文艺理论界得到了广泛且深入的讨论。学者或关注于经典本身的特质,或关注于权力的作用,或关注于经典化的进程,等等。不同的思考起点,导致不同的着重点,从而得到一个不同的定义。

《论经典》
作为文学研究者,是不能回避这些争鸣的。这些争鸣本身均是从现象至本质的研究,各有其合理性,同时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譬如:从特质出发,研究对象的哪些内在特质尚未被充分阐释?从权力出发,哪些研究对象的现世作用尚未被开发?从经典化的进程出发,哪些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面产生了非文学的误读或过度阐释?
这均涉及到文学研究的命题,是可以借助和发挥的地方。
我们有必要来看一下经典的定义。
詹福瑞先生将中、西方对于经典涵义的概括之后提出,“经典”的规定条件当有三点:其一经典是指传统的传世精神产品;其二经典应该是杰出的精神产品;其三经典具有典范的文化价值和意义。[1]
如就此规定再进行提炼,会发现有三组核心词:其一为传统的传世的,其二为杰出的精神产品,其三则需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以传统、传世而言,应是经过长时间的传播,换言之,经典是经过时间检验以区分经典与时尚,确定经典的“普适性”,使经典脱离某时某世的限制,从而具有永久价值;从杰出的精神产品来说,这贯穿了作者、文本、读者三种要素,其根本源自于作者的创作思考,最终以读者的意义阐释来显示其作为杰出精神产品的特性。
而所谓杰出者,是读者服膺于经典,并通过阅读来成就自我之思考,这也体现了经典的“权威性”;极高的文化价值指向经典文本本身的蕴藉,因文本对社会人生的表达深刻而典型,从而具有了“耐读性”,使读者百看不厌。
如果就此三条再作阐发,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必须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具有艺术上长久的生命力,能经得起一代代读者的阅读与阐释。这就对经典本身提出了要求,也成为经典的内在本质。詹先生以“传世性”“普适性”“权威性”“耐读性”予以概括。
童庆炳先生就经典的内部要素,做出解答。

《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首先,“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是建构文学经典的基础”,经典 “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也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其次,“文学作品的言说空间的大小,也是文学经典建构的必要条件”,“我们面对的作品思想意义比较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很多很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说不尽’”。[2]
童庆炳先生提出的两个要素是有层级的。文学的经典首先得是写人的, “文学”即“人学”,而文学经典想要写出“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就需要对人性有深入地挖掘,使读者获得真实的阅读体验,并生成共鸣。

《为什么读经典》
“言说空间”的提出,是针对于文本的思想意义而言的,需要经典文本本身所提出的命题具有普遍性、延续性,从而使得文本的阅读随时能够提供陌生感,保持常读常新的阅读体验,从而经得起多方位、多层次的解读与阐释。
从经典文本本身来说,以童先生所言之“人性心理结构”的“共同美”,是读者产生共鸣的基本条件,而此也是使文本具有传世性的条件,无共鸣则文本不可能传世,更不可能普适。不能触发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审美感发,就不会成为审美视野中的活体,无法跨越时间与空间,从而丧失生命力。
从言说空间来看,是以文本深度作为阐发基础,是产生“权威性”“耐读性”的前置因素。言说空间来源于作者的充分表达。充分表达是建立在作者本身思想的广博以及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入思考之上。
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会创作出有深度、广度的言说空间,才会建立起权威性的文本,引发常读常新的审美感受。
二

对于经典的探讨,尤其是经典化的探讨,更多起源于西方的文论研究。但经典的普适性,也使得经典的内在要求相对固定。产生于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经典,都有着很强的共性。
且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在经典这一理论产生之前,经典已经出现。如儒家的各种经典。这说明在中国古代已经有了认定文学经典的标准。

《“诗”与“仁”:孔子诗学思想研究》
孔子的“兴观群怨”一说,虽源自于对《诗经》的解说,但也是从接受角度概括了文学经典的功用价值。当此功用价值的评判标准反馈于创作之时,也就成为文学经典的内在规定,进而影响到诸多文体。
“兴”与“观”是相连且不可分割的。所谓“兴”者,朱熹云“感发意志”,冯宪光与付其林以“审美感发”[3]予以概括,从阅读层面来讲颇为合适。
“观”是两个层面的:其一,观文本所反映的现实,即郑玄“观风俗之盛衰”;其二,观作者自身的思想,即“以诗观志”。
如果说“兴”与“观”,还着重于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群”与“怨”更倾向于这种交互作用之后的阶段,体现在读者与社会之间的功用。
何为“群”?张载云“盖不为邪所以可群居”,朱熹云“和而不流”,这些解读,均放置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何为“怨”?古人多解为“怨而不怒”,以程颐所言,“怨”是一种“讥”“刺”,以张载所言,“怨”起于“人情”,是“正于礼义,所怨者当理”的批判。[4]
“兴观群怨”,四者之间联络有序,以兴为起,以怨为终。

《王夫之诗经学研究》
清人王夫之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而可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5]
王夫之对“兴观群怨”的阐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充分运用“兴观群怨”的功用,并将之综合。
王夫之所言的“于所兴而可观”“于所观而可兴”,这是深入阅读的表达:“兴”之后的 “观”,与 “观”之后的 “兴”。二者统一,形成螺旋上升式推进的阅读,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建构深入共鸣,触发深层思考,从而呈现出“深”而“审”的阅读体验。“兴” “观”之后,方有“群” “怨”。
而“群”与“怨”的结合,则着重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针对于不同的人群,因文学的作用而产生“不忘”与“益挚”的效果。王夫之以兴与观,打通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联,又以群与怨贯穿读者与现实,从而将文学的功用与价值完整体现。
“兴观群怨”是诗论,也可作为对文学艺术社会作用认识的总结。中国历代的学者都在丰富着这一理论的内涵。正如张杰在《从“兴观群怨”到“熏浸刺提”》一文中所说:“‘兴观群怨’在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有关阅读效果研究的理论的一种概括。”[6]冯梦龙在《喻世明言·绪》中写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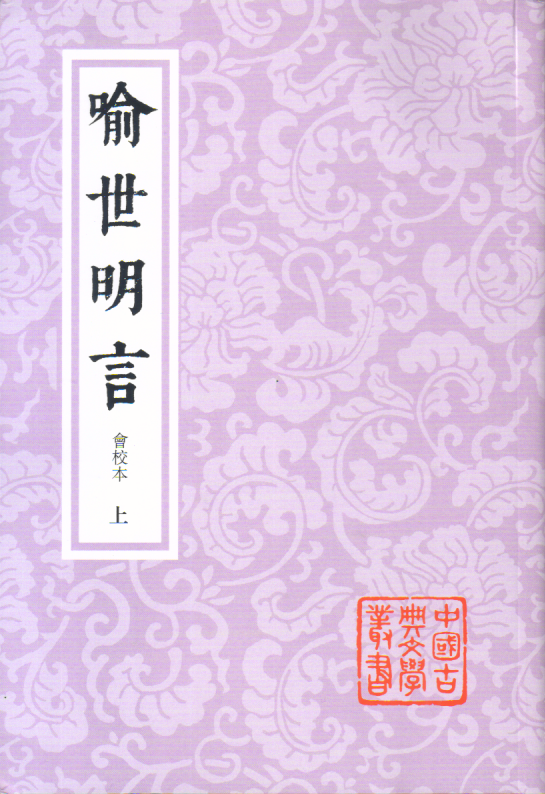
《喻世明言》会校本,冯梦龙编著,李金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9月版。
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7]
此种描述,正是小说进入“兴观群怨”的阅读效果的体现。
基于功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可以”,也就成为经典文本的内在要求,成为经典的评判原则。而如何达到“可以”,就有了面对人群、文体等因素的区分。
三

如汉赋、唐诗、宋词,“文变染乎世情”[8],明中叶后,文人的市民化与世俗化倾向,使得白话小说得以大发展,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得以兴盛,文学活动由传统的文人雅士走向市井,文学的主体产生变化。

《明代小说史》
王学左派的兴起,直至李贽童心说、汤显祖至情说的出现,使得文人第一次抛开了“文以载道”的创作条例,转而以人的自然性情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呈现出注重个体,注重真情的倾向。
小说作为一种独立于史传而存在的特性逐渐呈现,逐渐走出“羽翼信史而不违”[9]的创作要求。如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评价《三国志通俗演义》时认为其书“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而毕竟还有“留心损益”,[10]他已注意到历史小说的创作需要有虚构。
袁于令的认知更进一步,在《隋史遗文序》中,他写到:
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幕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11]
在这里,袁于令就史与小说的不同展开辨析,以“贵真”与“贵幻”加以区分。而贵幻,正是对小说虚构的本质特征的表现。这是小说发展的内在理路,同时也为作家的创作解缚。
针对于这种解缚,金圣叹从史与小说的分界谈及: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记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12]
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借“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来概括说明了史与小说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强调作家“削高补低”的创作自由。

《金圣叹全集》
这种自由创作的模式,使小说与史得以分离,也使得稗官野史的功用产生转移,在评价之时,“实”不再是标准,审美的功用逐渐体现,对于小说的内部规定逐步生成。
其一,白话小说的语言与阅读人群问题。
白话小说作为俗文学之一种,其俗字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用俗语;其二、适俗人。用俗语是适俗人的前置,适俗人是用俗语的目的。如冯梦龙就提及“宋人通俗,谐于里耳”[13],袁宏道在《西汉通俗演义·序》中也说“文不能通而俗可通”[14],白话小说语言的通俗化,是白话小说面对群体的必然要求,也是能让市井中人起兴的首要条件。
其二,涉及到小说创作主旨。
既然将市井中人作为主要的阅读群体,则小说就寄托了作家的创作目的。长久以来,小说一直为小道,其功能不过是供人娱乐,这种认知来源于孔子的言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15]这种看法延续良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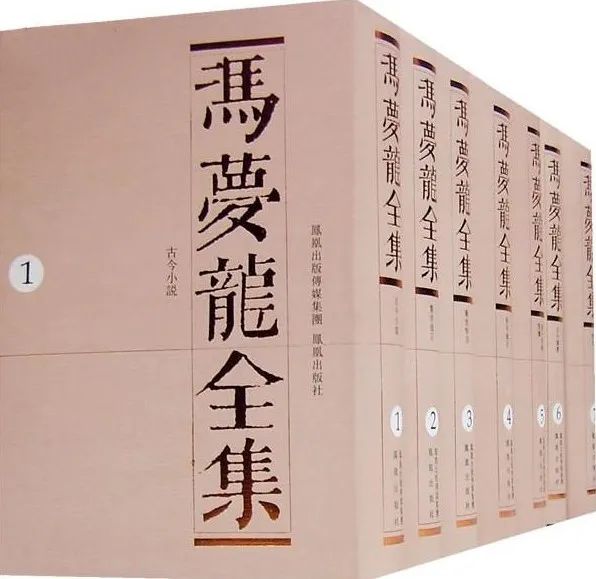
凤凰出版社版《冯梦龙全集》
至可一居士时,则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 [16]
在可一居士看来,小说有“六经国史之辅”的功效,可“导愚适俗”。
冯梦龙也借小说,来宣扬自己的认知,他在《情史序》中写到:“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17]他借小说以宣传自己的认知,此亦可视作另一种形式的载道。
其三,涉及到创作的批评理论。
批评理论的诞生,是对小说创作的归纳总结。李贽与金圣叹对此的论述较多。如李贽所提出的三个命题:“传神论”“妙处只是个情事逼真”以及“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批评论。[18]
前二者即是对小说的总结,从而演化成经典文本的必须;另一则是从评点的角度,提出评点者需要贯穿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命题,包括了对典型人物的塑造、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以及评点功能等的思考,其中的思考是非常深入的。

《贯华堂第五才子书》
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里,金圣叹可谓是一座高峰。他将“性格”作为评点术语,来进行文学人物批评,如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19]
对于有着近似性格的人,“犯中求避”,也能做到区分,如谈《水浒传》中的人物时,他讲到: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20]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能够做到“亲动心”,去体悟艺术人物,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并由此去生成人物的行为,所以能够做到“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的境界。
对此种写法,金圣叹借助于佛教语称之为“因缘生法”。在谈及结构论时,金圣叹以“倒插”“夹叙”“草蛇灰线”等诸多文法来进行概括,此等皆为以后的创作奠定理论的基础。

陈洪《金圣叹传》
当我们反思这些理论生成时,便会发现这是一个闭环。先有小说的创作,在创作中技法不断的丰富,思考不断的深入,而后产生理论,继而再指导创作。无论如何创作,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作者思考,易于引导读者阅读与接受,继而阐释。
从此角度来看“兴观群怨”,只要阅读,就会进入兴观群怨的阐释通道,与其说这是孔子的发现,不如说是孔子对自身阅读体验的总结。
这是基于文本与阅读,文本与社会之间关系所做出的,是阅读行为自然产生的现象,孔子所做的只是总结与命名。这种阅读的现象,是无分古今中外的。
正是这种自然而然产生的阅读体验的层级,才会出现经典与非经典的区别。我们去讨论经典的内部规定性,实质上是在对经典文本的解构与探讨的基础上寻找其中的规律。经典的内部规定性,就是对如何生成高等级的“兴观群怨”的规律性总结。
思考再进一步,“兴观群怨”是由文学而社会学的内容,是文学作为人学的体现,也是文学的功用与价值所在。由此也衍生出文学对人的审美、思维的提升。文学的审美、文学技法的运用、文学典型的塑造、情节的铺陈,无不是为了起兴服务,从而进入兴观群怨这一阅读通道。
这些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正可说明这种内部的规定性。而基于共性,与西方的经典的内涵,也可互相参照。
文本需要写到人性的深处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而此共鸣正可以“兴”来阐释。无论是李贽的“传神”“妙处只是个情事逼真”,还是金圣叹的“因缘生法”“亲动心”,都是立足于对人物真实的追求,从而进入到深入人物内心的创作。

《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
从言说空间而言,来源于作家的思考深度,也来源于作家的生活广度。只有具有了思想性的文本,才会经得起多层面、多方位的解读,从而起到“观”的作用。“群”与“怨”是建立在“兴”与“观”的基础之上,是深入阐释以后文学的社会效益。
注释:
[1] 詹福瑞《论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4页。[2] 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载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81-82页。
[3] 冯宪光 傅其林《文学经典的存在和认定》,载于《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38页。
[4]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577页。
[5] 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第3页。
[6] 张杰,《从“兴观群怨”到“熏浸刺提”》,《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7] 冯梦龙编著,东篱子解译,《喻世明言全鉴》,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1页。
[8] 刘勰著,韩泉欣校注,《文心雕龙》,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44页。
[9]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罗贯中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第17页。
[10] 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罗贯中著,沈伯俊校注,《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1] 袁于令,《隋史遗文·序》,《隋史遗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页。
[12] 金圣叹著,林乾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3、4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9页。
[13] 冯梦龙编著,东篱子解译,《喻世明言全鉴》,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1页。
[14] 袁宏道,《西汉开国演义·序》,甄伟著《西汉开国演义》,三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3页。
[15]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
[16] 冯梦龙著,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评点,韩欣主编,《名家评点冯梦龙三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页。
[17] 冯梦龙,《情史序》,冯骥才主编《中华散文精粹》(明清卷),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58页。
[18] 赖力行等编著,《中国古代文论》,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第225至226页。
[19]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施耐庵著,《水浒传》,齐鲁书社1991年出版,第20页。
[20]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施耐庵著,《水浒传》,齐鲁书社1991年出版,第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