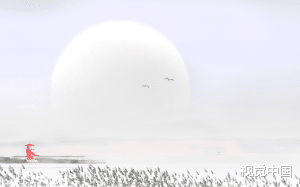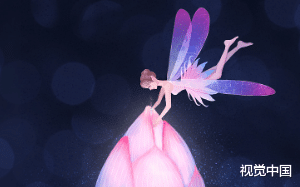从乞丐到将军,我等了殷琰五年,等来的却是他和权贵小姐的婚讯。
他面上征战在外,实则年年回京,只不过见的人从来不是我。
于是我不等了,转身另嫁他人。
可殷琰却后悔了。
我在他面前撕了婚书,任他像狗一样趴着拾那些红纸片。
我用一碗红花让殷琰绝后,他却说这样也好,只有我和他的孩子,才是他想要的。
呸,颠公。
1
怀远将军殷琰凯旋回朝那天,京城少有的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而我攥着一纸婚书,穿着自己唯一一套绸缎衣服,拼命探出头大喊:“殷琰——殷琰——”
一别五载,他从小乞丐一跃成为战功赫赫的怀远将军,腰上别着御赐的佩剑。
甲胄下的那张脸,熟悉又陌生。
殷琰停了马走到我面前,我听到周围有女子倒吸凉气,满是惊羡。
说殷琰丰神俊朗,又才华横溢,是不可多得的好郎君。
我扫了眼婚书上他的名字,喜滋滋一扬头,满目骄傲地迎上去:“殷琰……”
“别闹。”
面前的男人抿着唇,皱着眉,看起来有些不耐烦。
我愣住了。
我想过一百万种我和殷琰的相逢方式,唯独没有这种。
“待我安顿下来就会来找你的,别闹。”语罢,他牵着马就往前走去,甚至都吝啬给我一个眼神。
我正不知所措,身后传来一阵喧哗。
转头望去,刚好看到殷琰春风满面,伸手掀开了一顶华贵小轿的帘子。
那里面的女人露出一张小巧而温婉的脸,一见面前人,激动得又哭又笑。
我认识她,她是申国公府的嫡长女,秦清之。
一对璧人你侬我侬,卿卿我我,旁人都赞的是佳偶天成,郎情妾意。
那我呢?
八年前,是我以两个肉包子,将还是小乞丐的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
我收留了殷琰三年,直到全国征兵,他说自己要去报名参军。
“等我建功立业,你就是天下最幸福的将军夫人。”
殷琰将红纸写的婚书交到我手里,便匆匆离开了家。
如今他回来了,高兴见的人,却不是我。
2
殷琰进殿面了圣,接受完了所有大人的贺礼,还是没来见我。
他只派了个小随从来,要把我接到京中一间宅子里住着。
那时已是晌午,一早上的包子卖得差不多了,我准备收摊。
“我不去,”我叠起蒸笼,放到小推车上,“除非将军亲自来同我说。”
京中传闻鼎沸,说殷琰封了正三品昭毅将军,马上准备去申国公家下聘。
而那天半路冲出来拦着他的我,则成了所有人嘴里的疯婆子,拜金女,势利眼。
我需要一个解释。
“原来,琰哥哥同我说的那个青梅竹马,就是你。”秦清之围着斗篷蒙着面,越过随从,兜帽后的打量眼神落在我脸上。
“怎么,凭着一纸不知道是真的还是装的破婚书,你也敢摆架子?”
“不敢,”我低下头,抽出怀里那张红笺,展开在众人面前。
“只不过这上头,有殷将军亲手签字画押,秦姑娘不信的话,尽管找人来验。”
我不卑不亢,秦清之却气急败坏,伸手就要来抓那婚书:“这都不知多少年的东西,怎还做得数?”
我不喜不怒,闪身躲开,任由她身子前倾,一个不稳跌在地上,摔了个狗啃泥。
秦清之磕了膝盖,口角甚至微微渗出些血迹。
“你……你敢戏弄我?来人哪!把她给我绑起来!”
大约从未受过这样的对待,她气极了,也恨极了。
随从个个是成年大汉,听了命令立刻扑上来将我押住。
“谁敢!”
门外传来一声怒喝。
3
殷琰一袭绯袍而来,拨开人群,将我护在怀里,“是我来晚了,阿澈。”
熟悉的称呼和气息使我鼻头一酸,差点有眼泪流下。
我就知道他会来。
我内心雀跃,宛如一万只蝴蝶在心头扑扇着翅膀。
秦清之在殷琰背后哭诉:“我今日来请程姑娘去备好的宅子里歇息,可她竟然冷嘲热讽,故意叫我跌在地上……”
兜帽下若隐若现的啜泣声传来,我看着殷琰皱了皱眉头。
抱着我的手,松开了一点。
我的心也随之往下坠了一分。
他让人把秦清之送回府,又用一种有点儿小心翼翼的口气同我说:“我如今是正三品将军,申国公有意将独女许配给我,这是我的荣幸,不能拒绝……”
“不过你放心,等她嫁过来,我就马上以贵妾之礼抬你入府,绝不委屈你半点。”
我心头如遭雷劈,泪水簌簌滑落。
抖开红笺,将那上面“聘汝为妻”四个大黑字摆到他面前。
“殷琰,这写的是什么?”
我娘还活着的时候,曾经三番五次告诫我,宁为人妻,不做官妾。
毕竟,她当年守寡到最后,就是死在豪强逼她承欢的棍棒之下。
一个卖包子的女子,虽命如草芥,却也有尊严,也要自由。
可殷琰却别过头去,他不想看,也不敢看:“阿澈,这纸婚书,以后还是少拿出来比较好。”
4
那天,秦清之叫人放了话出去。
说谁来我这儿买包子,就是和她,和国公府过不去。
原本我的包子铺是全京城都闻名的味美价廉。
就连一些官大人家的随从,也每天排着队地来买我做的豆沙包。
如今,却再没人敢光顾我的生意。
我耗了大半个月,积攒的银钱见了底,最终只能入住殷琰为我置办的那处别院。
我知道,进了那屋子,我就再也不是堂堂正正开门做生意的程澈了。
而是殷琰见不得光的外室女。
我搬进来的第二天,殷琰就来陪我吃饭,似要补偿我。
他为我带了京城有名的酒楼菜色,炒大虾,笋丝鸡脯,烧香菇,还有一碗香气扑鼻的佛跳墙……在我面前摆了一桌。
我吸吸鼻子,口水忍不住分泌,转头刚好对上殷琰含着笑意的眼睛。
他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眼底含情的时候,更是光彩熠熠。
我猛地惊醒。
权力和财富养人,如今他是“马上潘安”,是京城炙手可热的新贵。
当年那个面黄肌瘦,饿得瑟缩在墙角,却仍旧如孤狼一般警惕的小乞丐,早就没了影。
殷琰伸手抚我的头:“小馋猫。”
我脑袋一歪,悄悄避开了,顾自举箸去夹菜吃。
他的笑容在脸上停滞片刻,随即垂下眼,去牵我空出来的那只手:“阿澈,之前冷了你,是我的不对。”
“清之小姐脾气,素日里跋扈了些,我也已经说过她,你以后安心住在这里就好。”
我心头微苦,连咽下去的饭菜,都觉得难吃不堪。
但还任由殷琰牵着手,任由他带着薄茧的指腹摩挲过我的手背。
他又掏出一个乌木盒子摆到我面前。
里头是一条项链,各种七彩水晶镶嵌其中,带着异域的别样之美。
“这是我在边关征战,扫荡城池时,为你带回来的。”
“无论走了多远,我一直都是念着你的,阿澈。”
我眼底微酸,吸了吸鼻子,任由殷琰如一条大狗似的,将脑袋埋在我颈间。
是啊,如今他是高官重臣,做什么事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扯多方,纷繁复杂。
可能是我这个平民女子太愚笨,太不懂事了。
我不懂殷琰的世界,至少不该再为他添乱。
5
那天,我欢欢喜喜地为殷琰做了一屉豆沙包。
他认真地捏起包子咬了一口,幸福地眯着眼:“还是最想娘子这一口。”
眉眼间的那点狡黠,让我恍惚间有回到旧时光的感叹。
我踮起脚亲他,将剩下的包子打包成一盒,递到殷琰手上。
可几天后,我没等到殷琰,却等到了秦清之。
她身边的下人将一个食盒摆到我面前。
里面,居然装着的全是那日我做给殷琰的豆沙包。
“这么粗糙的手艺,也好意思拿给琰哥哥。”
秦清之拈起一只包子,只咬了一口,就皱着眉把它扔到泥地上。
我拍桌而起,正准备一巴掌往她脸上扇,却在看到她周身首饰的那一刻,顿住了。
——那全是和我那条项链一模一样的彩色水晶。
只不过我只有一条碎钻组成的项链,而秦清之却有一整套头面。
水晶各个浑圆完整,华丽天成。
她身边的随从立刻介绍道:“这是将军一年亲手从塞外带回国公府上的,说是定亲礼物,全天下也只有这一套呢!”
巨大的悲伤从我心头倏地涌起,我甚至感觉有点眩晕,身体晃了一晃。
等一下……
“你说什么?一年前?”我注意到了那话里的言外之意,圆瞪着眼看向秦清之。
明明,我已经五年未见殷琰。
可他一年前就回过京城,却不来见我……
秦清之愣了一秒,随即脸上涌现出不可掩饰的得意:“怎么,琰哥哥回来,竟不见你这小青梅?”
“他每年都会回京复命,顺便看望我爹我娘,给我带些礼物,你这都不知道?”
6
远远地传来马蹄声,殷琰夺门而入,走向我的时候,竟生生推了秦清之一把。
秦清之跌在丫鬟怀中,抹起了眼泪:“你明明在府里还同我说,护着程澈全是逢场做戏,如今看来却是真的了!”
殷琰想来抱我的手,尴尬地停在了半空中。
我勾起一抹冷笑,轻轻后退一步:“不必了。”
原来这就是殷琰说的,记得我。
如今他有权有势,得佳人青睐,对待我,只消从手指缝里漏下一点好。
他以为这样,就足以使我感恩戴德。
“她同你说了什么?”殷琰的神色里带着显而易见的慌张。
我眼圈泛红,扬起手,一巴掌落在殷琰脸上,“既想要从前的情分,又想要今天的富贵。”
我死死盯着那张慌张又无措的脸,心头悲伤如潮水般翻滚涌起,“我祝你,一个也得不到。”
语罢,我撑着身子就往外走。
我宁可死在街头,也不要殷琰假惺惺地对我好。
身后传来秦清之委屈又尖锐的哭喊:“殷琰!你今天要是敢追她,我便和我爹说,拒了这门婚事!”
“一个破卖包子的,难道比得上我吗?”
7
我推门而去,任由衣冠不整,鬓发散乱的自己行走在街头,接受众人的注目。
殷琰没有追出来。
可笑我走出门去的那瞬间,还有一丝小小的希望。
如今也被浇灭了。
手腕上的银镯子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我伸手抚过上头的纹路,只觉心底一阵悲戚。
在她逝世的第十年,我终于走上了和她一样的路。
是我想错了,权贵男子,谁不想三妻四妾,看女人们为自己勾心斗角?
而其中最卑微,最落魄的我,被迫害得最惨,也是意料之中。
头疼愈演愈烈,我逐渐意识到不对劲。
眼前天地旋转,一切开始变得模糊。
我倒在了地上,意识慢慢消散而去。
陷入一片黑暗之前,我只记得自己,抓住了一方青色的衣角。
……
8
醒来时,我发觉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
一个面容慈祥的婆婆迎上来,为我递上温水:“姑娘醒了。”
我撑着身子勉强坐起:“我在哪儿?”
“这是徐主簿府上。”
我脑海里查无此人,只听木门吱呀一响,走进来一个体型瘦削,身量高挑的男子。
我瞪圆了眼:“阿行?”
这……这不是我还在京城开包子铺时,每天蹲在我旁边,给流浪儿们发白粥的男人吗?
我从前同他相识,他说他叫阿行,家中尚有积蓄,愿行善积德。
而现在,男人一身青色衣袍,头发朴素地用一方巾帕束起,看着我的眼神温柔又恳切。
“下官正七品詹事府主簿徐中行,见过姑娘。”
我眼神扫到他衣摆处明显的折痕,立即明白了前因后果,挣扎着身子就要下床行礼。
老婆婆将我温柔地扶回床上歇息,只听徐中行说:“姑娘依旧唤我阿行就好,不必拘礼。”
我端详着他的模样,一时间眼圈都有些红。
“大夫说了,姑娘体内有极重的毒素,此毒常见于日常吃食中,无色无味,积累三五天就能置人于死地。”
徐中行的这一句话,却让我彻底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