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年往事》
作者:九枝雪

简介:
[双重生]秦漱始终不能释怀,前世杀了她的人是宋郇。
彼时她是景元公主,唤他一声太傅。
她死在了景年间的那个雪天,她说:“若有来世,便不要再遇见太傅了……”
却不知道自那以后,宋郇最厌恶的便是冬日。
一朝重生,她本想远离前世的结局,也远离宋郇。
可那人踏着白玉石阶一步步朝她走过来,神情克制:“秦漱,你就是仗着我喜欢你,有恃无恐。”
后来,那人问她:“秦漱,你可知道在记忆里反反复复摹刻着一个人的过往是什么滋味儿?”
他满目猩红,扯出个惨淡的笑来:“是会疯的。”
......
宋郇以为一瓶假死药能帮秦漱逃出桎梏,却不想被人换成了鸩毒。
自此,宋郇的天再也没亮过,秉直端肃的人变得乖戾,他蛰伏在这座肮脏的城替她报仇,害过她的无人能得善终。
兰因逝,死生同,死在宋郇手上的人,也包括他自己……
精彩节选:
秦漱始终不能释怀,前世杀了她的人是宋郇。
所以她知道,人人畏惧至甚的鸩毒,是甜的。
宋郇将毒酒端给她的时候,面上的坦若还清晰如昨。
“时至今日,公主仍旧觉得陛下适合这个位置吗?”昏黄的灯影将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宋郇坐在那里,纵使在这个行军帐中,背脊依旧柄直,像他这个人一样。
秦漱闻言心中苦笑,她费尽心力辅佐上位的皇弟,亲手将她送往与北夏和亲的这条路上。
宋郇有此问,秦漱一时答不上话来。
她端起酒杯,青瓷墨纹将莹白的手指衬得更为显眼。
宋郇的视线在那指尖上头多停了片刻才不动声色地移开。
“虎符是个催命的东西。”
宋郇开口,点到为止,秦漱知道他这话的意思,却也只能哑声。
无论他和皇弟两方,谁得到虎符,都免不了一战,而此时的大楚,再经不住折腾了。
帐子外头,风嚎拉扯出绵长的尾音,雪迟了一个月,终于落在了今日。
秦漱想要再给自己添一杯酒,斜里伸过来一只手,将酒壶挪开:“酒多伤身,殿下少饮些罢。”
“太傅也喝些,暖暖身子。”
宋郇将酒壶放置一旁,像是没听见秦漱的话一样,秦漱早就习惯了他这个性子,也不多言。
朝政上,两个人的政见分道扬镳,却能平平和和地坐下来说一说话,大概只是因为这个人是宋郇了。
记忆里,从宋郇做了她和皇弟的太傅后,一直都是这般不苟言笑的模样。
秦漱掩在宽袍里的手按了按小腹,忍下一阵刺痛。
对面的宋郇垂着眼,面色如常。
看着宋郇面前始终空着的杯子,一瞬间,秦漱仿佛明白过了什么,眼中闪过悲色和自嘲,问了宋郇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太傅到底是谁的人?”
她尽量压着声音里剧痛带来的颤抖,这一生眼看着要走到尽处,秦漱迫切地想知道答案。
宋郇抬起眼,看到秦漱的脸色,皱了皱眉,却仍是回道:“微臣是大楚百姓的人。”
秦漱盯着他,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表情,想要从这人面上看出些什么,却终是徒劳。
宋郇果然是宋郇,这回答滴水不漏。
秦漱嘲弄地笑了出来:“太傅果真谨慎,亲手下毒竟也不放心吗?相识一场,好歹...让我死个明白。”
宋郇眼底沉静:“公主好好睡上一觉,等醒过来,便不必再为这些事扰心了。”
一命呜呼,可不就是不必再扰心了,倒也落得个清净,秦漱想笑,喉咙里却涌上来一股温热。
暗红顺着嘴角落在衣襟上,繁杂的绣纹上像开了一朵朵红梅,刺眼也夺目。
恍惚间,秦漱看到对面的人豁然起身,衣袖带倒了桌上的酒壶,这可不似他往日的行止。
胸腹间袭来的剧痛,让秦漱眼前发黑,她身子晃了晃,接着便落在了宋郇的怀里。
“秦漱!”这许是错觉,宋郇向来循规蹈矩,恪守君臣之礼,除‘公主’外,何曾连名带姓地叫过她秦漱。
她仰起头,宋郇终于不是那副淡然的模样,看向她的眼神也带着失措。
到这个时候,他还在她面前做戏,是因为还没能从她口中探得虎符的下落?
也或是担心万一她死里逃生,好回来报复吗?
倒也合衬他周密的性子。
秦漱心底的苦涩蔓延开,细细密密的疼让她渐失清明。
她拽着他的衣襟,宋郇顺着她的力道低下头,听见她开口,破碎的声音在耳边断断续续地响起:“太傅,我这一生...都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秦漱的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清:“若有来世...便不要再...遇见太傅了...”
“秦漱,不准睡!”
她还能听见声音,可眼前已经是茫茫的一片黑。
“来人!快宣太医!”身子陡然被人抱起,这是秦漱第一次从宋郇的语气里听出惶恐。
失去意识前,她甚至还有心思在心里奚落起宋郇,人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真是如此,他抱着本公主这等若柳之姿,手臂竟还抖得厉害,没用得很。
秦漱终究没能踏上北夏的土地,死在了大楚那个最冷的冬日里。
黄花梨鸾凤呈祥瑶台镜里,一女子用镂雕桃木梳顺着垂落在胸前的青丝。
腮凝新荔,芙蓉如面柳如眉,只神色间尚有些怔忪。
正是秦漱。
重生了已有月余,秦漱仍旧不敢置信,会有这样离奇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不曾料到,一朝睁眼,竟回到了七年前,景元甘年。
皇弟还不是皇上,而宋郇也还不是太傅,一切也都还没开始。
秦漱仍旧是这大楚最受宠爱的景元公主。
能用国号册封的公主,在这皇城里只她一个,其盛宠一时无两,难有旁人可比。
秦漱弃了扎人眼的车辇,换了辆寻常马车,来了咸安城里最大的酒楼。
她来等一个人,一个前世将她护于身前,用背脊挡住乱箭,换她活下来的人。
秦漱至今都忘不了箭矢刺透皮肉的声音,背后的少年一声不吭,护着她逃出追杀,才轰然倒下了马。
少年的手还护在自己身前,怕穿身而过的箭伤到她,一身宦官服已经辨不出本来颜色,整只手却被染得鲜红。
往日寡言的少年笑得像个要讨赏的孩子,他说:“公主,辛执没让您有事。”
少年再也没能张开眼,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
秦漱喝了口酒,让眼中的热意褪去。
前世的今日,若自己没有选择救宋郇,而救了辛执,一切是不是会不一样。
酒楼下如期传来骂声,一群纨绔打扮的人围着一个少年,那少年一袭青衫洗得发白,被人推攘着后退,形容狼狈,神态间却不见半分窘迫。
“凭你个庶出的下贱东西,也配进太学书院?我呸!”
“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货色,奴婢生的就永远都是奴,父亲仁慈,给你请先生允你识字,你却还不知天高地厚想进太学书院?”
“识相的话,便主动同父亲说你不想进学,否则,我便让你晓得什么是尊卑!”
“还不给本公子跪下认错!”
任凭他们打骂,那少年也一声不吭。
唯有一双眼漆黑淡漠得古井无波。
秦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一个少年,可此刻的宋郇就是给她这种感觉。
仿佛置身于尘世外,像是个旁观的人。
秦漱看着楼下的少年,心想若自己是那群纨绔,见到被欺负的人还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定然也想揍他。
秦漱移开眼,外头接着便传来拳头落在身上的闷响声。
前世,秦漱就是这个时候从窗子一跃而下,挡在了宋郇身前,虽没露出公主的身份,可秦漱的功夫与太子同师,习自禁卫军统领郭权。
哪里是这群只会武弄些拳脚的纨绔能比的。
那时少年一低眉眼,便乱了秦漱的心。
外头的拳脚声不断,秦漱缓步走下了楼。
被人围着的宋郇抬眼看过来,同秦漱的视线相撞。
秦漱的步子不停,走近那群人,而后转了方向,向小巷子里行去。
她头也没回,便也没能看到见她离去时,身后少年眼中的不解还有讶然。
打人的声音突然停了一瞬,接着又响起一阵骂声:“你这贱奴还敢瞪人?”
“给我打,给我狠狠的打!”
叫嚣着最狠的是宋家嫡子宋明,他向来看不惯宋郇,可偏偏父亲总是拿这个庶子同自己比较学问,凭他这个娼妇生的也配同自己相提并论?
宋明想到昨日父亲考教他的功课,他吭吭哧哧地答不出来,宋郇却得了父亲赞赏,害得自己得了一顿好骂。
念及此,宋明手下的力道更重。
刚刚这贱奴还敢瞪自己,那眼神的狠厉吓得宋明心中一抖。
他反应过后觉着失了面子,竟叫这个庶子给吓住了,恼羞成怒之下便狠狠地踹向宋郇:“你个娼妇生的贱种,公子我就该把你眼睛剜了!”
宋郇看着秦漱的身影随着一个踉跄逃窜的孩子进了小巷,他心底猛然升起一股戾气,伸手挡住宋明踹过来的脚,抬手一掀,便将宋明掀了过去。
宋明一行人都叫这变故惊得愣住了,没想到一直被宋明踩在脚下的庶子,竟然敢还手,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宋明气得脸色涨红,指着宋郇便要破口大骂,却看到宋郇眼神时,像被什么恐怖的东西扼住了喉咙,硬生生地将话吞了回去。
众人便瞧见方才还被他们拳打脚踢的人慢慢站起身来,明明还是方才那个人,可莫名的,凡是对上他那双眼的人,都觉得周身变的寒凉。
不由自主地退后一步,面面相觑。
有脚步声从巷子里传来,宋郇像是有所觉般看过去,便瞧见秦漱又追着那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跑了出来。
前头那个小身影朝宋郇这群人跑过来。
宋郇看向秦漱,听见她对着孩子喊:“你给我站住!”
下意识地便伸出手拽住这个孩子。
这孩子脸上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看不出样貌,瞧起来也很瘦弱,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
却在宋郇抓住他时出手如电,攻向宋郇的穴道,迫使他松手。
那穴道被攻击时极疼,换做寻常人,早便松了手,也不知是不是同他受伤过重有关,出手少了力道,宋郇只抿了抿唇,攥住他的手丝毫未松。
眼见着身后的秦漱要追上来,那孩子小脸一沉,抱着宋郇便跳到湖里。
这时节,湖水冷得渗人,浅一点的都结了层薄冰。
好人掉下去也只怕也要去了半条命,更何况这个身受重伤的孩子。
秦漱伸出手抓了个空,眼见着辛执和宋郇掉在了湖里,气得咬牙。
没想到辛执将她当做追杀他的人,浅浅地交手几招,寻了机会就往人多的地方跑。
宋郇和辛执两个都不会水,她这回出宫又没带宫人,只有一个车夫,还是她出门随手雇的,现下找人已经来不及了。
宋郇淹死了便罢了,活该他欠自己一条命。
却不能不管辛执。
宋明等人怎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也真的干了落井下石的事儿。
这帮孙子搬起岸边观赏的石板,往水里扔。
两个不会水的人被砸得十分狼狈,宋郇的额头被砸出了血,宋明扔的石头没有准头,落在辛执身上的也不少,小小的人儿在湖水里没了声息。
秦漱不敢耽搁,将大氅扔在地上,跳进湖里前抽个功夫,几脚便将宋明等人一个不落地踹进了湖里。
任由他们哭天喊地的在水里扑腾。
宋明在水里浮浮沉沉,叫得最响,嗓子都吓得破了音:“救命!救...我!本公子的爹...唔...是礼部...侍郎...”
秦漱游过宋明身侧的时候,顺手将他脑袋按进水里,留下一句话:“本公主的爹是皇上!”
她可没忘前世这人还妄想用见不得人的手段,想要娶她。
宋明:“你他...他娘的...唔...”
秦漱急着救人,没有注意到宋郇眼中一闪而过的笑意。
秦漱将辛执的脑袋架到自己肩上,辛执眼皮动了动,掀开一条缝,又没了意识,秦漱拖着他便往岸上游。
却被一道力气扯住了,她回过头,见到被落下的宋郇手紧紧地抓着辛执不放,神色幽幽地看过来一眼。
秦漱想像按宋明一样将他也按进水里,辛执却这个时候突然抽搐起来。
救人要紧。
秦漱心一横,不甘不愿地伸出手,拽着宋郇,状似不经意地在他身上拧了几下,如愿地看见他疼得变了脸色闷哼出声,才算心满意足。
她一边带着人往岸上游,一边眼神也欠奉一个,没什么诚意地道歉:“抱歉,并非有意,救人要紧,公子担待些。”
“无碍,多谢姑娘相救。”宋郇的眼光一错不错地锁在她的侧脸上,贪恋地描摹她的轮廓。
秦漱若是这时候回头,便能看见宋郇眼中浓得化不开的情愫。
好不容易才将两人拉上了岸,秦漱正要背起昏死过去的辛执,却被宋郇抢了先:“臣...他有些沉,我来。”
宋郇将辛执抱上马车,见他还没动,秦漱便道:“孤男寡女同坐一辆马车于理不合,就劳公子自行回去罢。”
秦漱将自己身上的大氅盖在辛执身上,一旁的宋郇见此眼神暗了暗,又听秦漱这话,索性径直在秦漱对面坐了下来。
他垂下眼皮,敛住眼中神色:“天寒地冻,在下自来体弱,若是自行回去,怕是会生得一场大病,还望姑娘慈心,送在下一程。”
男女同乘一辆马车实则算不得什么,大楚的民风也未曾封固至此。
可说这话的人换做了宋郇,就足够叫秦漱讶异。
前世,回忆起宋郇给她做太傅的那段日子,被他说教最多的,便是‘不合礼数’,在她面前永远都是一副圣人模样,
她如今听得这话,不禁在心底‘呸’了一声,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秦漱正琢磨着要不要将这人踹下去,宋郇隔着车帘朝外道:“劳烦,礼部侍郎府。”
“好嘞!”
车夫已经扬了马鞭。
秦漱气得噎住,年少时候的宋郇竟这般不要脸皮?同后世沉稳淡漠的那个太傅简直判若两人。
马车里的两人无人开口,都各揣着心事。
只有车辙压在路上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格外明显。
即便知道宋郇还未曾做过那些事,两人也还未曾走到敌对的路上。
可念及过往,秦漱还是不可避免的迁怒这个时候的宋郇。
她突然想到一件事,宋郇如今还是个白身,未曾入仕,若是能让他无法入朝为官,岂不可以一劳永逸?
转念一想,这事儿有些难办,父皇是个惜才的君主,尤其似宋郇这样心有饕餮,且怀大才之人,于此时的大楚而言,无疑于如虎添翼。
依着宋郇的本事,只要他想,早晚有一日会入得了父皇的眼。
那么一切又要回到原点,如前世一般。
要么...杀了他?
宋郇看着秦漱眼中变幻莫测,看向他的神色不善。
虽不知她在思量什么,但下意识地觉察到危险。
于是秦漱便瞧见对面的人,抬起手握成拳,掩在嘴边咳嗽起来,像是要把肺腑都咳出来一般,缓了好半晌,才止住声音。
坐在那里脸色苍白,任谁也看得出他虚弱得没什么力气,勉强撑着才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
秦漱的手松了又握,前世军帐中的太傅和此刻的少年宋郇不停地在她脑中交错。
末了,她暗自叹了口气,又在心底里骂起自己心软。
若是从前的宋郇站在她面前,她可以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可此时的宋郇,还什么都没做。
马车停了下来,宋郇起身,身形还尚有不稳,扶着车板缓了缓神才站稳。
宋郇转过来,朝她拱手:“在下宋郇,多谢姑娘救命之恩,若有来日,必定相报。”
秦漱冷眼看着,连眼角都没动,她想起前世同宋郇说的最后一句话,‘若有来世,再不要遇见他了。’
可见老天还是喜欢同人逆着来的。
她肃着脸不吭声,送客的意思很明显了。
宋郇下了车,看着马车远去,在拐角处消失,才抬了步子往府中去,脚下的步子沉稳,哪有方才在马车里虚弱的模样。
秦漱将辛执安置在了公主府中,她看着眼前这个鼻青脸肿的人,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救错了人,毕竟长大后的辛执,同小时候还是有些差别的。
她伸出一根手指,按住辛执的嘴角往上挑,直到露出了一对儿虎牙,秦漱才确定了这人就是辛执无疑。
一次,辛执曾提起过,他在进宫前,曾躲在一处巷子里,看到了一位公子在楚阳酒楼下被一位姑娘搭救。
说的正是秦漱和宋郇。
若非如此,此番怕是不能这么顺利地寻得到他。
辛执是被人偷偷卖进宫的,有人趁着他重伤昏迷,将他卖去做了宦官,那一年他十三岁。
纵然有一身武艺,可在宫里那个吃人的地方,也有的是叫人生不如死的法子。
辛执性子倔强,年岁不大,偏还生了一身傲骨,宫里的老太监用尽了腌臜的法子折磨得他奄奄一息。
辛执被扔进了废弃的宫殿里,宫里许多受了刑的宫人,若活不下去了,便扔在那里任其自生自灭,埋着的白骨怕是有尺余厚,不曾听说有谁活着出来。
除了辛执。
他遇见了秦漱。
那一年宋郇做了秦漱的太傅,陡然间却像换了个人。
秦漱近前一步,宋郇便束着手后退一步。
神色也没了往时的温和,疏离之意再明显不过。
“宋郇,你怎么了?做了我的太傅,我们便可以日日相见了,你不高兴吗?”
秦漱从宋郇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宋郇开口,刻板又规矩:“臣不知殿下是公主之尊,先前若有失礼之处,还望公主恕罪。”
“宋郇,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公主,难道我就不是那个同你相知相识的奚和了吗?”
奚和是她的小字,被赐封号前,只有父皇私下里这么唤她,秦漱将这名字告诉了宋郇,心意早便昭然若揭。
宋郇这才抬眼,那双如同点了墨的眸子里,好似将一些东西压了下去,不过片刻的涌动,复又沉寂。
“论身份,臣不过是宋家的一个庶子,您是这大楚最尊贵的公主,有君臣之别。”
“若论礼数,我为公主师长,亦不可逾矩。”
秦漱的眼睛里有了泪意:“宋郇,我不要你做我的太傅了。”
宋郇又垂下眼,强迫自己不去看她:“公主,圣旨已下,君无戏言。”
秦漱闻言竟气得推了他一把:“我说不要你做太傅就不要!”
之后便跑了出去。
宋郇沉静地看着那个一身华服哭着跑走的姑娘,宽袖下交握的手,指关节被捏得发白,面上却不露的分毫异样。
便是那一次,秦漱躲去了废弃的宫殿,恰巧救了险些被人折磨死的辛执。
公主府中,负责照顾辛执的小宫女彼雀慌乱地跑了出来,去报掌事姑姑:“姑姑,不...不见了。”
掌事姑姑南矜见状沉下脸训斥:“慌慌张张的是什么体统,还当是在...咳...”
南矜的话及时转了个弯又继续问道:“还不说清楚些,什么不见了?”
彼雀闻言矮身福了个礼,才又道:“禀姑姑,公主带回来的那位受伤的小公子不见了。”
南矜闻言也瞪了眼,戳了一把彼雀的额头:“你个蠢雀儿,怎的不早些说清楚!”
随着话音消失,人也往秦漱的寝殿去了。
“公主,不好了,不...不见了。”
秦漱放下手中的话本子,扬了扬下巴:“什么不见了?”
南矜苦着脸答:“您带回来的那位小公子不见了。”
出乎南矜意料的,秦漱又拿起话本,伸出一只手朝房梁上指了指:“那儿找了吗?”
南矜随着她的手翻了翻眼皮,福身行了个礼,默默地退了出去。
秦漱看着话本子,却在想南矜、彼雀她们的事。
这些人是在她很小的时候,随着父皇赏下的公主府一并送进来的。
尤记得当时父皇说了句很模糊的话,‘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制命也’。
当时她趴在父皇的御案上,歪着头:“奚和不懂。”
父皇只摸了摸她的脑袋道:“有些事,要自己去看,才看得清楚,悟得明白。”
在看到不过盏茶间,南矜便回来复命时,秦漱若有所思。
“禀公主,小公子的确睡在房梁上。”
秦漱点了点头,让她退下。
秦漱知晓辛执的习惯,他是个谨慎性子,若非是也跃上房梁查探,是决计发现不了他的。
再者,安置辛执的百福阁,距离她的永宁殿路程不短,寻常脚力即便是快些走,也要两刻左右。
而南矜却不到盏茶间便走了一个来回,且气息不乱,绝非寻常宫人。
自己前世极少住在公主府中,多半都住在宫中的庆和殿里,便也极少见到公主府的这群人。
前一世自己活得还真是糊涂,竟错过了身边的内里乾坤。
辛执醒了,一直躲在房梁上,滴水未进。
叫秦漱意外的是,虽说他本事不小,但若是趁人不备逃出去也不是不可能,脚上功夫可是他最擅长的。
但是他连百福阁的门都没出去,就叫人耐人寻味了。
看来真得好好思量思量她这个深藏不露的公主府了。
秦漱来的时候,还没进院子,便听见一道珠翠般的声音:“真不吃?这片皮乳猪可谓是外脆里嫩,随上薄饼,蘸上酱汁,鲜的人能吞了舌头去,你真不尝尝?”
里头没有说话声。
小姑娘又问:“你叫什么,还不曾听见你开口说话,莫不是个哑巴...”
“你爹。”
小姑娘:“......”
秦漱听得暗自好笑,举步进去了,便瞧见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一身淡粉宫装,梳了两个髻,拖着食盘,那上头正是片皮乳猪,还有一应小菜。
这情形,倒真像是哄骗孩子的牙人。
辛执扒着房梁,露出个脑袋,警惕地看着刚进来的秦漱。
小宫女被辛执一噎,脸上哽得涨红,见她进来,忙朝她福了个身:“奴婢彼雀,见过公主。”
随即她苦着脸:“公主,任奴婢如何说,这位小公子也不肯进食。”
“放下吧。”秦漱摆摆手让人退下。
辛执瞅准机会,运了轻功便往门口处蹿,方才还在桌边摆放吃食的彼雀,瞧不出如何动作,眨眼间便移到了门口,正笑嘻嘻地堵在辛执的面前。
“你怎的不长记性,跑了几回了,哪回成功了,要我说,多吃些东西,没准就有力气跑了呢。”
辛执抿着嘴,一声不吭地又回到房梁上。
秦漱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这些人的身手,若按照自己前世的眼光来看,此刻还算不上绝顶高手,但也绝不是泛泛之辈。
彼雀没有刻意掩藏实力,那么南矜呢,她是故意用了极短的功夫,往来百福阁和她的永宁殿吗?
彼雀朝她福了身道:“公主放心,奴婢就守在外头。”
这话与其是说给秦漱的,不如说是说给辛执听了,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
房梁上的辛执听见彼雀对秦漱的称呼,讶异地看了秦漱一眼,抿了抿唇,还是没有作声,神情倒不似先前对着彼雀那般戒备。
秦漱也不急着让他下来,自顾地坐了下来为自己斟起了茶。
悠闲的样子倒让辛执眼中疑惑渐深。
他见秦漱拿出一张纸,展开放在桌上,缓声开口:“若你想躲过追杀,留在公主府是最好的选择。”
“签下这张死契,你便是公主府的人。”
“那些追杀你的人还要掂量掂量,惹不惹得起本宫这个麻烦。”
秦漱这话说得不错,辛执签下死契,再命南矜等人想办法将消息放出去,让那些要杀辛执的人闻声而却步。
毕竟江湖争端再重要,也没有人愿意因此惹上皇家这个麻烦,尤其是,这个人还是当朝最受宠的嫡公主。
辛执还是不做声,秦漱也不催他,一口一口地饮着茶,这让秦漱想起从前的宋郇。
他也总是这个漫不经心的模样,越是淡漠,对手就越拿不准他的心思,举手投足间扰得对手心神不定,最后,总是叫他如了愿。
秦漱不知何时竟学了他这个习惯。
一想便有些烦心,蓦地撂了杯子,磕在桌子的声响叫房梁上的人一惊,传来衣料摩擦的声音,辛执继而跃了下来。
他咬破了手,看也没看就在那张死契上按下了手印。
秦漱见此反倒惊讶了:“你不怀疑我要害你?”
辛执垂着的眼抬了起来:“我记得你,是你将我从湖里救上来的。”
秦漱点点头,拿了死契便欲离开:“你安心在这里住下罢,缺了什么尽管找南矜要。”
“等一下。”辛执开口将她叫住。
秦漱回过头,便看见他拽着衣角,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
见秦漱看过来,辛执更是扭捏,看得出来,是狠了狠心才开了口:“我、我什么时候侍、侍候您?”
“啊?”秦漱一时没反应过来,但瞧见辛执这副样子,才猛地意识到了他说的是什么。
她忍笑忍得肚子疼,转过身去,朝后头摆摆手,强忍着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且等着罢!”
辛执的事交给了南矜,很快办妥。
在秦漱带着辛执出门时,连暗中窥探的人都没敢近前,躲得远远的。
秦漱前世多半守在宫里,如今倒是很喜欢街市里的烟火气。
带着辛执彼雀出来逛了半日,瞧什么都新鲜。
几人寻了一处茶肆吃点心。
彼雀去停马车,却在门外同人吵了起来。
声音传到了茶肆里。
“明明我家马车先停的,凭什么给你让路?”
一个男子的声音也不甘示弱:“你这姑娘也忒不讲理,明明是我家马车先到了,是你硬将我们挤开的。”
彼雀扬着嗓子:“嗯,那就是姑娘我的本事!”
“你、你好生不讲道理!”
这声音有些耳熟,秦漱一时竟没想起来,顺着窗望出去,看到站在不远处的宋郇时,才反应过来,同彼雀吵架的这个小厮,正是宋郇的小跟班侍墨。
许是有所觉,宋郇也看了过来。
秦漱将眼神撇开,盯着手里的茶盏,没想到,竟会遇见宋郇。
她听见侍墨同宋郇道:“公子,这姑娘忒不讲理了...”
宋郇看着窗子里的人,同侍墨道:“道歉。”
侍墨:“...啊?”
“给这位姑娘道歉。”
侍墨明显不甘,却也不能违了宋郇的意思,委屈巴巴地同彼雀道:“姑娘,对不住了。”
对方示弱,彼雀语气也不似方才那样咄咄逼人:“罢了,我还有差事,不同你多计较了。”
秦漱见她回来,瞪了她一眼,彼雀能同侍墨不讲道理,在秦漱这却明显晓得自己理亏,讨好地对秦漱笑笑:“姑娘,外头那位公子一直瞧着您呢。”
秦漱没回头,余光里也瞥见一抹青色身影,站在外头。
“不识得的人,理他作甚。”
外头,侍墨见自家公子定定地看着窗子里的那个姑娘出神,便问道:“公子可识得这位姑娘?”
宋郇沉默了片刻,才转了身,径直走在前头:“还不曾。”
秦漱余光里的青衫消失了,她也没能品出这茶的滋味儿。
秦漱注意到侍墨手中捧着的书匣子,算算时候,宋郇就是这段日子进的太学书院,而后崭露头角,一举中了状元,得了父皇青睐,继而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可秦漱不能将手伸进书院,那样定会惹了父皇的眼,反倒更容易叫父皇注意到宋郇这个人。
不如...给宋郇找个对手。
她想起宋郇曾说过的一个人,丞相家的小儿子柳知尘。
此人也进了书院,不过是在宋郇后一年进的学。
当时秦漱还同宋郇玩笑说:“柳丞相怕是没少打点。”
宋郇却道:“许是世人都看走了眼。”
他曾用 ‘慧极’两字评价过柳知尘此人。
柳知尘算得上是秦漱的玩伴,她倒是没瞧出来他哪里能得了宋郇这么高的评价,不过依着宋郇的眼力,许是真有什么过人之处,且死马当作活马医罢,左右现下也没旁的法子了。
得让柳知尘今年就进太学书院,否则依着宋郇的能耐,占了天时的便宜,先站稳了脚,还有柳知尘什么事儿。
柳知尘的行踪不算难找。
彼雀抬眼看着‘清和赌坊’四个大字的时候,还有些懵。
秦漱率先进了门,赌坊的小厮是个有眼力的,看她打扮,便知其非富即贵。
脸上笑容可掬,引着秦漱进门。
秦漱道:“柳家公子呢?”
一听她是来寻人的,小厮脸上的笑意淡了些,却仍是恭敬地同秦漱打着哈哈:“姑娘说笑了,这清和赌坊每日进出百来人,小的不知道哪位是柳家公子。”
秦漱道:“人傻钱多那个。”
小厮只是笑,不敢接这话。
秦漱也不与他多言,冲彼雀扬了扬下巴。
彼雀会意,从怀中掏出...一枚铜板。
秦漱嘴角抽了抽,盯着彼雀不动。
在看到秦漱发凉的眼神中,彼雀又将铜板默默地揣了回去,换成了一锭银子,递给小厮时,她脸上表情还十分肉痛。
小厮得了银子,脸上的笑更真切几分,伸出手指,偷偷朝三楼私阁的方向指了指,而后退下。
秦漱进去的时候,在一群人里一眼便瞧见了柳知尘。
他头上带着的那颗东珠委实耀眼,就差把‘爷有钱,快来坑我’几个字写在脑门上了。
柳知尘也瞧见了她,直起身子朝她招手,露出一口白牙笑得很傻:“元元!”
秦漱:“......”若非有事寻他,秦漱想调头就走。
柳家人都是好相貌,秦漱觉着,这样的好颜色生在柳知尘身上着实是浪费了。
秦漱还算了解几分他的性子,遂朝他招了招手。
柳知尘见状,手里的银子往桌上一扔,颠颠地跑了过来。
“元元?”
秦漱尽量叫自己笑得不像个拐孩童的人牙子:“柳知尘,我来找你堵一把。”
柳知尘闻言眼睛都亮了:“好!赌什么?”
秦漱正要说话,便又听他开口:“先说好,输了你可不能耍赖。”
见他还竖起手指还要再开条件,秦漱不耐烦了:“我拿东郊的那座宅子做赌。”
柳知尘闻言‘唰’地一下将竖起的手指收了回去,快得只看见一道残影。
迫不及待地应了下来,生怕秦漱反悔:“好,一言为定。”
秦漱东郊的那座宅子柳知尘觊觎很久,倒不是因着那宅子内里的奢华。
而是因为那宅子里的机关,是工部的偃师们费时近三年才完工的。
柳知尘胡闹惯了,柳丞相经常带着人去抓他,偏偏寻常地方拦不住柳丞相的人,每次他和一群狐朋狗友们正值兴起时,便被他老子提溜回府。
柳知尘叫苦连天。
如此,他便盯上了秦漱的那座宅子,机关一开,他老子总没胆子拆了公主的私宅吧。
他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同秦漱道:“元元你说,要赌什么。”
秦漱道:“别在这谈,去东郊那座宅子里谈。”
一路上,秦漱曾几度怀疑,当时宋郇是不是在骗自己,她怎么也没看出来这个看起来不大聪明的柳知尘有什么过人之处。
否则怎么三言两语地就被自己骗到了东郊。
顺利得让秦漱心里没底。
柳知尘进了宅子,像进了自家屋子一样,寻了个地方就坐了下来,仰着头十分享受。
还招呼秦漱:“元元,你要同我赌什么?”
秦漱没答话,反倒退后一步,在门外站定,用十分怜悯的眼神看了一眼柳知尘。
这眼神看得柳知尘心里发毛,他后知后觉的站起来,门口却突然落下了一道精铁制的门。 柳知尘豁然回头,这间房子的四周也同时落下铁墙,将退路堵得严严实实。
他跑到门口,将脸嵌道栏杆的空隙里,一张俊脸被挤得变形:“元元~这是干嘛啊~”
这模样不忍直视,秦漱背过身去:“这屋子里的书随你看,要什么书就招呼人拿,什么时候你进了太学书院,我便什么时候将你放出去,柳丞相那边我自会去说。”
柳知尘在身后哀嚎:“元元~我不要宅子了!”
秦漱深吸一口气,想起宋郇对他的评价,在心里暗道:宋郇,你这厮当时要是在诓我,咱俩旧仇未了又添新账,到时候定要与你一并清算。
秦漱回了公主府,南矜已经等在了垂花门处:“公主,宫中传了话来,娘娘请您回宫一趟,看起来很急,来人已催了两回。”
秦漱当下便想到了一件事,皇弟秦屿此时还不是太子,大楚的几位皇子还在暗戳戳地奔着储君的位置使劲儿。
明里都是一副谦和模样,兄友弟恭的表象怕是只为了演给父皇一个人看。
母后急着召自己进宫,想来也只有那桩事了,秦漱脸上的表情淡了许多。
秦屿同母后娘家的表兄以作学问为由出了宫,表兄萧戟带着他去了青楼寻乐子,为争一女子,竟与人大打出手。
对方有些武艺在身,两人偷偷来这种地方,自然不敢多带人手,眼见着要吃了亏,秦屿便抽出匕首捅了那人,那公子当场毙命。
死的那个是个官家公子,还有些来头,与清河崔氏沾些亲。
如此便不好等闲视之,这事往小里说是两家孩子争执,若落在那些文人墨客嘴里,少说也要挑起一段争端,添上些笔墨。
拉扯大些,便是皇家不容世家。
大楚是马背上打下来的王朝,才刚刚安定几年,前朝的血还未干透,此时不宜再起争端。
更何况,秦屿想做太子,他的身上便不能有能被人指摘的话柄。
故而,秦漱便成了那个替罪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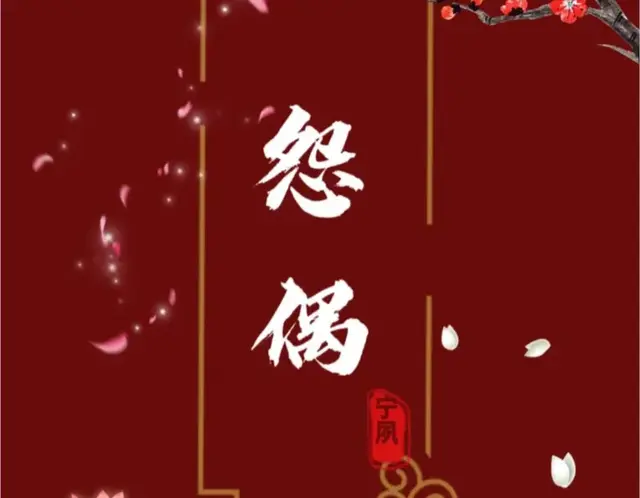






看不进去,不太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