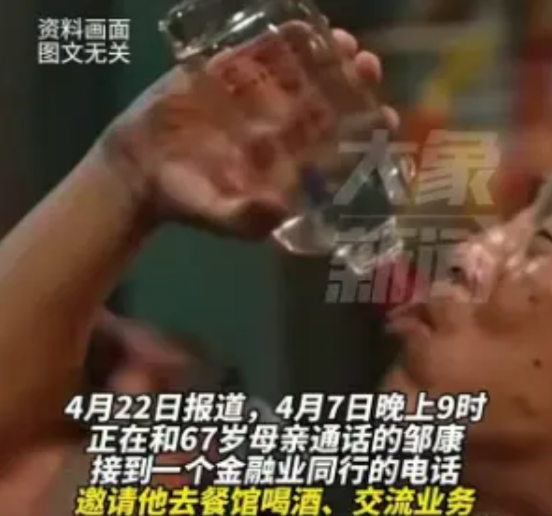1991年,内蒙古一位牧民手持一枚神秘金灿灿的铁牌请求鉴定,经权威机构验证竟是稀世古物,按规定必须上交国家。牧民满口答应择日呈递,谁知次日专家登门收取时,赫然发现牧民妻子的双腕各戴着一只沉甸甸的金镯,那耀眼的金光晃得专家眼前发黑,血压瞬间飙升。 【消息源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志编纂委员会《内蒙古文物志》1993年内部刊印本;辽金史研究会《契丹考古研究论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国家文物局1991-199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简报(未公开档案)】 八月的克鲁伦河畔,草尖上的露珠还没被太阳晒干,高斌已经赶着羊群走出了两里地。这个蒙古族汉子弯腰掬水洗脸时,突然被河床里一道金光晃了眼——拳头大的鎏金铜牌半埋在泥沙里,上面刻着他从没见过的蝌蚪文。"该不会是前些年地质队落下的零件?"他用牙咬了咬边缘,留下两道新鲜的牙印,铜牌上"右皮室详稳"五个契丹大字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三天后,旗文物管理所的老刘端着放大镜直咂嘴:"清代蒙古王爷的腰带扣嘛,你看这鎏金..."话音未落,高斌媳妇乌云其木格已经麻利地用装奶豆腐的皮囊包起铜牌:"那能换两头母羊不?"老刘扶了扶眼镜腿,没敢接话。他们不知道,此刻铜牌照片正在呼和浩特考古所的灯箱上被三个专家围着,张默副研究员手里的《辽史·兵卫志》翻得哗哗响:"这是辽代皮室军的调兵信符!《武经总要》里记载过,见符如见萧太后..." 当张默带着盖红头文件的征集通知书赶到牧场时,高斌家蒙古包前正飘着股奇怪的焦糊味。炉子里躺着团不成形的金疙瘩,乌云其木格攥着剪下来的铜牌残片小声嘀咕:"专家说值钱的就是这些字,俺特意留了巴掌大的..."张默蹲在炉灰前捡出几粒金渣的手直发抖,旁边巴特尔干部赶紧打圆场:"老高啊,你这跟熔了成吉思汗的苏鲁锭有啥区别?"高斌搓着满是老茧的手:"羊圈塌了半年没钱修,娃的学费还欠着..." 后来事情出现了戏剧性转机。统战部会议室里,巴特尔把五百元奖金推到桌前:"钱不多,但够解燃眉之急。"张默则捧着装金渣的密封袋苦笑:"318克,正好是辽代一斤的重量..."最让人意外的是那块被剪下的契丹文残片——后来成为研究辽代军事制度的关键物证,现存内蒙古博物院玻璃展柜里,标签上特意标注着"牧民高斌夫妇捐赠"。 第二年春天,草原上贴满了蒙汉双语的《捡获文物奖励办法》。高斌家新修的砖瓦房前,几个牧民用他当例子教育孩子:"看见奇怪东西别乱咬,先去喊巴特尔叔叔!"而千里之外的考古所里,张默正在给新出土的辽代铜器做拓片,忽然对同事笑道:"这纹路,像不像老高家炉子上的焦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