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神仪式,可汗特意命人为我打造铁架,供我祁舞。
我忍着剧痛,跳完舞蹈。
铁架下点了篝火。
冰火两重天,我脚底溃烂。
舞毕,我被冷汗浸湿。
有人指着我的脚,嫌弃带血的祭神不祥。
曾对我关怀备至的可汗坐在王座,笑着喝下一碗烈酒。
“让她再跳一遍就是。”
1
我对上一双绿油油的眼睛,绷紧精神。
“真珠。”
低沉的声音让狼群有些躁动,篝火边,破延冲我挑眉,“你求求我,我就把它们赶走。”
我沉默不语,默默对峙着,一点不敢松懈。
上次御马时,他也是如此。
我信了他,大声求饶。
结果他一鞭子抽在马腿上,然后勒住缰绳停下。
我死死地抱着马脖,马疯狂跳跃。
我被甩在地上。
马拖着我跑了许久,摩得后背鲜血直流。
他欣赏着我的狼狈,在马快控制不住的时候迫使它停下。
“真珠,学了这么久,怎么还是这么笨?”
我气若游丝,倒在破延脚边。
他命人将我送回毡帐。
片刻后,破延拿着一坛烈酒闯进来。
“真珠,有伤口就要治疗,你这一身光滑的肌肤留了疤不好看。”
我半死不活地趴在毯子上。
不能挣扎,也挣扎不了。
就像破延刚将我带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他宠我入骨。
会亲自喂羊乳给我,狩猎也不去,就乘马陪我在草原上狂奔。
部落的一个俟斤一箭射穿我们面前的野兔。
邀请他一起狩猎。
他搂着我的腰。
从侧篓里抽出一支箭,擦着俟斤耳边,射向他身后的旱獭。
一箭穿心。
他捂着我的眼睛,似笑非笑,“看不到本王正在与可敦培养感情吗?”
咦——
四周传来调笑的声音,无一不在打趣。
我几乎是一张白纸,任由破延在上面填着色彩。
红也是,黑也是。
烈酒整坛倒在我的背上,连着里衣刺进我的肉里,血和酒混着流下。
我疼得喘不上气,只能用手抓紧毯子打颤。
那一刻,我以为我要死了。
破延拍拍我的脸,手指点在我的背上,碾压。
我已经痛到麻木。
“真珠,你真好看。”
“尤其是香汗淋漓,红着眼看我的时候。”
我松开攥着毛毯的手,嘶哑地问:“为什么?”
破延猛地松手,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眼尾带着一抹红。
“你说呢真珠?辜负真心的人要吞一万根银针。”
“你这么聪明,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嗷呜——”
我陡然回神。
没有理会破延的话,轻移着步子试图靠近篝火。
狼群会回避火光,这也是我唯一能够脱身的法子。
破延的衣带在风中猎猎作响。
每一下,都像索命的钩子插在我的心尖。
我掐着手心,每一步都挪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分神。
破延却不时发出动静。
狼群要攻不攻。
我仿佛站在一根钢丝上,进退两难。
而钢丝的操控者,还乐此不疲地拨弄,颇有兴致地观赏着我的胆怯和惊慌。
我对过去的记忆有些模糊。
只记得第一日来部落的时候。
我看了两眼羊圈里刚生下来的小羊羔。
破延就宠溺地,用哄小孩儿那般的语气说:“喜欢?改天让人给你捉一只小狼崽去。”
我不好意思地垂眸,无声地表示拒绝。
破延也不强求,就带着我闲逛。
除了商议部落大事,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我。
2
他们都说,破延看上我了,要迎娶我做可敦。
我不明白。
明明我身材矮小、相貌平庸、性格内敛,为什么他偏偏会看上我。
我只能尽可能地收好我的心。
直到一次集会,宗族代表联合上奏,建议可汗繁衍子嗣。
破延没有理会。
晚上抱着我时,他说:“真珠,你不愿,本王是不会碰你的。”
那时,他身边除了我没有别人。
“那王位怎么办?”我还有些天真。
“到时候传给特勒就是。”
他拍拍我的头,语气里带着随意。
后来,我答应了他的求爱。
他对我的好比之前更甚。
记忆中,父母的样子渐渐模糊,我从小游牧的草原也逐渐淡去,甚至我都觉得我的语音也和大家格格不入。
破延看出我的窘迫和恐慌。
他用半年的时间,亲自教我怎么写字,怎么说话。
一遍又一遍地带着我巡视领地。
他告诉我,有他在,我就不会没有家。
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他在我的唇角落下一吻。
我始终记得。
那天,太阳从南边落下,撒了满地的金光。
破延压不住向上的嘴角。
他说:“下次大节,我一定要让你终生难忘。”
确实。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
僵持时间久了。
破延许是觉得无趣,转身离开。
我擦着火滚落在地上。
发丝被燎起,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从篝火堆里抽出一根带着火光的木棒,狼群多了几分退意。
渐渐,一只银灰色的狼转身,狼群隐匿在黑暗中。
我松了一口气。
手上传来灼痛感,木棒从我手中脱落。
水泡和黑灰黏在手心,我的手又疼又肿。
在部落里,可汗的喜好完全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比如,从前对我恭敬有加的女仆,肆意踩踏我晾晒好的皮毛。
我去取饭的时候,厨役端出一盘带血的羊肉,连着血倒在我的头顶。
“真珠小姐,我一时手滑,你不会介意吧?”
想必是他们特地弄来的羊血,满满当当灌了我一身。
黏糊糊的血将粘住我的皮肤和衣服,羊膻味直冲鼻尖。
有几个人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寒冬腊月,他们将我丢进结冰的湖里,戏谑地调侃:
“真珠小姐,可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片心意,好好在湖里清洗干净。”
破延也会适时“施恩”。
他不顾众人意愿,推举我在祭神台上跳舞祈福。
他很了解我,我四肢僵直。
根本跳不了美丽柔和的舞蹈。
“真珠,不要拒绝,这是你的荣幸。”
他亲自给我换上舞衣,动作温柔。
冰凉的银链触碰到我的身体,是彻骨的寒。
尖帽扣在我头上,发夹擦着我的头皮划过。
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我光脚站在他专门命人打造的铁架上。
脚底和铁架粘在一起,每一次抬脚都像掉了一层皮。
展臂,跳跃。
脚底铁架时而冰冷,时而滚烫。
仔细看的话,铁架上峰林着刺尖。
一朵朵血花在我的脚下绽放。
有人指着我的脚,嫌弃带血的祭神不祥。
破延坐在王座,笑着喝下一碗烈酒。
“让她再跳一遍就是。”
我数不清转了多少圈,一头栽倒在地上。
头破血流。
3
破延止住笑,起身把我抱回毡帐。
昏睡之际,我隐约看到一个面容不清的男子,温柔地抚上我的额角,轻轻擦拭伤口处的污脏。
到了晚上,一个穿着宽袖衫、大长裙的丫头进来。
她给我处理伤口的时候,我刚好醒来。
“你……是?”
她看向我的脸,有些迟疑,“奴婢是来伺候夫人的。”
“夫人看起来格外娇小,怎么受这么多伤?”
她叹了口气,任劳任怨地替我煮药、包扎。
她忙活完了,坐在角落,盯着北处看。
我躺在毯子上,看着她时而难过,时而庆幸,最终蜷缩成一团,躺在地上。
半夜,我发起高烧。
侍女哭倒在床边。
“夫人,我去求可汗,给你请巫医,他们都说巫医厉害,可以接人骨,改记忆,你一定要坚持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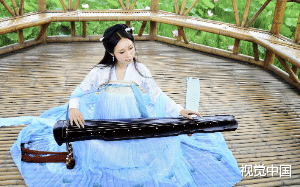








还可以,男的挺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