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六岁时救下的少年,摇身一变,成了高门贵子。
而我,从他明媒正娶的妻,变成被困在一方偏院的妾。
二十六岁这一年,我死在相府后院凌乱的杂草堆上。
他却在我尸体旁枯坐一夜。
一夜白头。
但是谢隽,负心的人,合该孤独终老,痛不欲生。
【1】
我生产那日,下了好大的雨。
我浑身是血地躺在床上,撕裂般的疼痛夹杂着无法忍受的寒冷。
稳婆在我耳边焦急地催促我使劲,我却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
突然有人冲进来大喊,
“侯爷说弃母保小,不必在意薛姨娘的生死!”
听见来人的话,稳婆手中力道突然增大,在我的小腹处揉搓。
剧烈的疼痛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
我再也忍受不住,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可惜没有人在意我的感受。
稳婆和大夫只想让我早点生下孩子,好向谢隽复命。
我突然好想回家。
尽管我无父无母,家中早已空无一人。
眼前仿佛出现了临川的老家,茅檐低小,溪边青草。
破落的院子中,我正熬着草药,含笑看着眼前的少年。
少年的面容很是模糊,看不清他的脸,我的心上总感觉缺了一角。
下一瞬,伴随着婴儿高亢的啼哭声,下人欢喜的恭贺声。
我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像是做了一个冗长的梦。
梦里,我终于看清了少年的面容。
正是谢隽。
梦里的我想要阻止,却还是无法改变我救下谢隽的事实。
我只是临川乡间的一个农女,救下谢隽后与他日久深情。
谢隽说他被仇家追杀,体力不济晕倒在乡野路边。
我将他带回家中悉心照料,在相处中与他日久深情。
谢隽说他是江湖中人,家境贫寒,但仍想给我一场体面的婚礼。
他便去镇上员外郎家做苦工,得来的工钱攒了许久,才从秀坊一位好心的绣娘那儿换来一小块金线绣的红盖头。
成婚那日,谢隽近乎虔诚地掀开盖头,目光灼灼。
“芳意,此生我非卿不娶,愿与卿白头到老,恩爱不疑。”
我恍若幽灵般看着这一切,痛苦地想要上前阻止。
却只是徒劳。
因为这不是幸福的开始,而是我一切绝望的源头。
成婚不过一年,京中便来了人。
那时我才知道,我的枕边人不是江湖少侠,而是谢侯的幼子。
因为不满谢侯让他尚公主,谢隽便赌气离府。
但时间久了,谢侯终是惦念儿子,承诺只要谢隽回府,便不再强迫他的婚事。
仆从恭敬地向谢隽转述谢侯的意思,谢隽在此时转头看向我。
他对我郑重承诺道:“芳意,你在家等我,我会禀明父亲,风风光光迎你回府做我的妻子。”
谢隽笑起来时有一颗小虎牙,眉眼间充斥着少年人风发意气,让人不自觉地想要接近。
我对谢隽的话深信不疑,“好,我等你回来。”
却不料,再见面,已是三年后。
谢隽虽是接了我回府,却是以妾礼,府中人唤我薛姨娘。
一晃三年,明明是同样的容颜,谢隽却再也不像他了。
眉眼阴郁,眼底无情,嫌恶地看着我穿的粗布烂衫。
反倒是他身侧国色天香,一身绫罗绸缎的女子,与我宛如云泥之别。
后来我才知道,谢隽身侧站着的,正是即将与他成婚的九公主。
他们这般,才能算作天作之合。
【2】
我在第五日的清晨醒来。
初为人母的本能让我下意识地寻找孩子。
送饭的丫鬟不耐地放下食盒,嘲讽道:“薛姨娘还是省点力气,若不是公主心善,念着姨娘诞下公子的功劳,这会儿姨娘怕是早就一命呜呼了。”
好似没听懂丫鬟的讽刺般,我焦急地上前,“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呢?”
丫鬟甩开我的手,皱着眉后退几步,“姨娘就别惦记着小公子了,如今小公子能养在公主膝下,是几世修来的福气,要是回到你这样的生母身边,那才是毁了小公子一辈子。”
丫鬟头也不回地走了,临走时还不忘告诉我,公主不想我接近小公子,让我无事别往她的屋里去。
剩下我失魂落魄地呆愣在原地。
若是谢隽从一开始就厌恶我至此,那为何他还要接我回府?
我自小便知晓,我这样身份的人,在那些权贵眼中就如草芥。
我曾见过村子里最美的姑娘,被员外郎家的公子看中纳妾。
接亲那日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好不风光。
可不到一年,那姑娘便被一卷草席扔到了荒山之上。
美其名曰,员外郎家公子心善,让姑娘落叶归根。
所以,我一早便知晓我与谢隽之间巨大的鸿沟。
即使他负了我,弃我于敝屣,我也不会再去寻他。
离了谁,这日子都照样过。
更何况,我卑微的出身在谢隽眼中就是污点,甚至连光明正大站在他身边的资格都没有。
可等我想通的时候想要走时,谢隽却拦在我的面前,“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你若是走了,岂不是让天下人骂我是负心汉?”
我记起谢隽迎娶九公主那日。
天家姻缘,整个侯府喜气洋洋,与有荣焉。
谢隽那日竟意外的好颜色,在宾客间觥筹交错。
身外妾室,连观礼的资格都没有,谢隽差人传话,让我第二日去给九公主磕头敬茶。
而我与谢隽成婚时,只是简单地拜了天地。
乡亲们送了几两香油,十几个鸡蛋,还有两只大母鸡。
就是我们婚礼上的全部。
虽然简朴,但红烛亮了整夜,我只觉得无比幸福。
谢隽,大概是不愿记起这样寒酸的婚礼吧,所以才会在与九公主成婚时,那样的扬眉吐气。
我吃着送来的,早就馊了的饭食,心中还存了些幻想。
到底我为谢隽生下了孩子,若日子长些,我再去求他,他应当能让我看孩子一眼。
只远远一眼。
如此想着,那些残羹冷炙似乎也不是如此难以下咽了。
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求谢隽,九公主派人让我过去一趟。
九公主素来看不上我,入府后见谢隽对我冷淡,便也放任我自生自灭。
或许在她眼中,捏死我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犯不上让谢隽觉得她肚量狭小,连一个妾室都容不下。
侯府中只有我们二人,她越是如明珠耀眼得宠,就越衬得我上不了台面。
所以我并不知晓她唤我去做什么。
【3】
九公主的房中生着名贵的暖香,闻之沁人心脾,摆着一件又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珍品。
谢隽也在,就坐在九公主的身侧。
可此时,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只被九公主手中怀抱的婴儿吸引。
十月怀胎,只一眼,我便生出了无边的眷恋与温情。
九公主连个眼神都不曾施舍给我,只有她身边的嬷嬷满脸不屑道:“大胆薛姨娘,公主体恤你刚生产不与你计较,你却僭越无礼,尊卑不分,竟连请安的本分都忘了,简直是胆大包天!”
我想起那日送饭的丫鬟特意说道,公主不想我见小公子,叫我不许往公主屋里去。
我只觉无力,那丫鬟我瞧着眼生,更何况府中人人避我如蛇蝎,只想踩我一脚,怎么可能替我作证?
“奴婢…..知错。”
最初的骄傲和自尊早就被谢隽一次又一次的打压踩在脚下,我明白我的身后空无一人。
九公主满意地勾了勾唇角。
嬷嬷吩咐赏我二十大板,公主笑吟吟地抬了抬手,“念在薛姨娘是初犯,又刚生下公子,便免去一半刑罚,侯爷,您说呢?”
我眼眸未抬,听见谢隽冷淡的声音在上座响起,“随你,你高兴就好。”
九公主娇羞地半倚在谢隽怀中,仿佛一对璧人。
我一直能感受到九公主对我淡淡的敌意,毕竟侯府中除了她,就只有我一个女人。
天底下哪个女子不希望自己的夫君只爱自己一人?
可是她是公主,自恃尊贵清高,谢隽又表现得对我十分厌恶。
若不是谢隽因为年少时不懂事与我拜了天地,不想担上始乱终弃的骂名,谢隽也不会捏着鼻子接我入府。
重重的板子一下又一下地落在我的身上,疼得我几欲晕死过去。
“侯爷…..”
九公主小心翼翼地看着谢隽的神情,谢隽神色如旧,“无妨,做错了事就该受罚,你是侯府主母,这些小事你做主就好。”
九公主终于彻底放下心来,好心情地让人将我抬回院中,转而与谢隽郎情妾意。
面对这样的凉薄之人,我该哭的。
可我怎么也哭不出来。
毕竟从我怀上这个孩子开始,我便知道谢隽的心从来都是偏的。
那日谢隽喝醉了酒,趁着醉意闯进我的房中。
下人们说,侯爷是与公主置气,一时气急又不忍失态伤害公主,才来我屋中泄火。
我自是认可这样的说辞。
因为那晚的谢隽格外凶狠。
他在我的身上起起伏伏,没有丝毫怜惜,只是在肆意地发泄欲望,不曾与我说过一句话。
就好像曾经温柔青涩的谢隽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天还没亮,谢隽就匆匆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赶着去哄哭了一夜的公主。
正是那一夜,我有了孩子。
公主知道后又发了好大的火,谢隽直接派人送来了一碗堕胎药。
我不可置信地望着来人端来的药,手脚冰凉。
我挣开束缚,跑去他的书房门口跪下,“侯爷,我自知身份卑微,可我腹中的孩子是您的骨血,求您让我留下他吧!”
我哭得心碎。
明明曾经的他视我如珍宝,不仅不让我干一点活,磕碰着一星半点都急得不得了。
如今的谢隽却只是冷漠地俯视着我,“既然知道自己的身份,你有什么资格替本侯生儿育女,有你这样出身的母亲,孩子生下来也会为人轻视。”
我睁大眼睛看他,执拗地不肯走。
若不是后来公主想通了要抱走我的孩子放在自己身边教养,我便真的做不成母亲了。
谢隽柔和地揽着九公主的细腰,“委屈你了,若是你不开心,一碗药打发了便是。”
九公主满眼柔情,“怎会?毕竟是侯爷您的骨血,就当是为了我与侯爷今后的孩子积德了。”
这两人谈笑间便决定我孩子的生死,但只要能让我的孩子活下来,我无所谓尊严。
【4】
当夜,我发起了高烧。
九公主为了彰显仁慈,让大夫草草开了几副药。
我气若游丝地趴在床上,早没有了力气。
不会有人在意我的生死。
谢隽更是如此。
甚至于我若是死了,侯府只会庆幸,谢隽是九公主的驸马,而非一个乡野村妇的相公。
我猛地吐出几口鲜血来。
模糊间,我隐约看见床边像是坐了一个人。
我连抬眼的力气都没有,心中想着,兴许只是我的幻觉罢了。
来人却说话了,“早知道生下孩子会吃那么多苦头,何必当初?”
谢隽竟然会来看我?
很多时候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谢隽那样嫌弃我的出身,还要坚持与我拜了天地,甚至将我接回侯府。
既然变心得如此彻底,为何不做得更绝一些?
以他的权势,派人去临川悄无声息地抹杀了我,岂不是一了百了?
思及此,我艰难地扯了扯嘴角,“多谢侯爷关心,我左右是活不了多久了,只要小公子能得九公主善待,我多吃些苦头又何妨?”
我看得清楚,九公主深爱谢隽,自然会爱屋及乌。
她只是厌恶我横插在她与谢隽之间,并非真的会对谢隽的孩子下手。
谢隽坐在黑暗中不说话,我感受不到他的情绪。
他的眼神一直停留在我身上,终于,他问道:“可上过药了?”
我愣住,不知道如何回答。
又听见谢隽低低叹了一口气,一勺药汤被递来我的嘴边。
屋里静得可怕,窗外小雨淅淅沥沥,似有脚步声传来。
“记得把药喝了。”
留下这句话后,谢隽匆匆走了。
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我的一场梦。
谢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脚步声似乎只是侍卫巡夜发出的声响,谢隽走后,屋内又陷入一片死寂。
我盯着那碗汤药缓缓升起的雾气,看了许久。
直到雾气散去,变得冰凉。
九公主派了人来,说我不必再去请安了,安心养伤。
说到底,就是见我时日无多,让我不必再心存幻想去看孩子。
侯府上下难道都已经知道,我快要死了吗?
那谢隽呢?
昨夜他来我屋中,是否也是因为知晓我快死了,大发慈悲来看我一眼?
我自嘲地笑笑。
又是一年冬天,我的屋子里依旧没有棉被和炭火。
我身上盖的这床破旧的红被,还是我从老家带过来。
和谢隽成婚之前,我将爱意缝进了这床红被之中。
谢隽派人来接我那日,我满心欢喜收拾好不多的细软,以为从此便苦尽甘来,能和心爱之人相守一生。
如今,这床红被早已褪色,破烂,无论我再如何缝补,都回不到最初的样子了。
往年的冬天,我都紧紧裹着被子把自己蜷缩起来,心里祈祷着寒冷的冬天能快些过去。
今年,我却好想去看看外头的景色。
谢隽给我的院子是最偏僻的,四四方方的天怎么瞧,都让人觉得窒息。
隔得远远地,我看见谢隽陪着九公主踏雪寻梅。
谢隽脸上的温柔与笑意我许久都没见过了,九公主含羞带怯,满心都是与心上人厮守的欢愉。
听侯府的下人们说,九公主对小公子很好,就像亲子一样。
我默默转身离开了。
【5】
人人都说,我一个乡野村妇,在侯府享了这么多年的福,是几世修来的福气。
没有富贵命,享了不属于自己的富贵,就会遭天谴反噬。
大夫断言,我怕是过不去这个冬天了。
我的屋子里破天荒添置了崭新的棉被,过冬的炭火,让我记住主子的恩德。
我活了二十六年。
这二十六年里,我得到的温暖不多。
一次是我十六岁与谢隽成婚那日,一次便是我二十六岁临死前的棉被与炭火。
炭火升起温暖细腻的烟,我盖着厚厚的被子躺在软榻之上。
可我清晰地觉察到,我的身子怎么都热不起来。
好似一块冰块。
半梦半醒间,有人在摩挲我的手心,“怎的如此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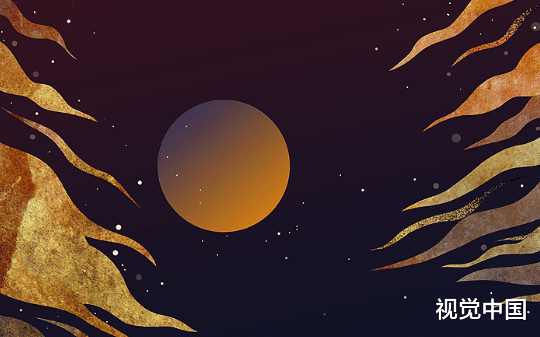







这种人最是自私,他不愿意承认自己薄情寡义,便装出一副深情的模样,把自己也一起骗了。
男主对女主的感情,更像是透过一个媒介,去缅怀年少干净的自我,他不在于对女主的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甚至女主的孩子也是他谋利的工具,他对女主的爱,大概就是放手给女主自由,有点良心但不多
这种男人是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女人爱上他就是倒了八辈子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