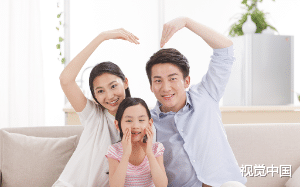白鸽礼堂外的海棠花开了,彼时我八十岁,望着沐浴在阳光下的葳蕤花瓣,流下思恋的泪水。
1
我第一次见到允忠,是我十四岁,在报纸上。
男人笔端执锐,谈吐犀利,直指时代弊端。
当时我刚刚回国不久,接受外国新思想的洗涤,有大把大把的想法想要实践,却苦于身边没有志同道合的人。
尤其,我还是个女子。
但遇见他后,便完全不一样了。
被父母安排进入南华中学后,偶然的机会,看到他在舞台上表演,男扮女装却不显女气,将故事核心和主人公的内心展露无疑。
那时允忠二十岁,我偷偷去后台看过他的侧脸。
非常非常年轻俊美。
我当时想和他搭讪来着,但他行色匆匆,眼里闪着灼灼光辉,并没心思留意我。
可我不生气,并且觉得,允忠就是我要寻找的,志同道合的人。
2
十六岁,国家领土被侵占一经传出,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沸腾,我作为学生干部,也站在讲台上,呼吁学生们进行还击。
那时,我不知道允忠那天回国。
只知道他创办思悟社的时候,我自告奋勇地成了第一批社员的其中之一。
社团活动每天如火如荼,而且立下社员不准恋爱的规矩。
所以允忠和我在这期间保持着单纯的学长和学妹的关系,他坚持独身主义,我则标榜新时代女性的民主自由。
那时候,民族危亡是挂在我们心上的石头,谁都没有想过恋爱这类事。
那年,全国因不平等权益被割让的消息不胫而走,掀起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当时我们在学校,都是男生和女生中的领头羊,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商议,最终决定由他和其他多名学生代表去游行。
但我们都高估了学生的力量。
学生的力量是瘦弱的,渺小的,随便就可以被嚣张势力扼杀掉。
就算当时我们在社会上已经有一部分影响力,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我和其他学生代表在外面紧张地等候,里面时常传出他们受刑但绝不认罪的消息。我们内心焦灼,并且紧急向各方有能力的人奔走。
但现实再次狠狠打击了我们,军阀势力虽然知道我们无罪,但就是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压制我们,这种霸权统领一切的现象,是我深恶痛绝的。
丧权辱国、一退再退,男儿们的铮铮铁骨早在金碧辉煌的屋子里和软玉生香的美人堆里被击穿。
就在代表们被押解的第四十天,我们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我赴京寻找名满京都的龚律师,请求他帮我们起诉。
当然龚律师并不好请,而且让他相信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也是不容易的。
我赴京的时候,兜里揣着爱国志士募捐的律师费,还有我搜集的证据,包括各大登报的新闻以及学生代表受辱的照片。
龚律师很通情达理,他睿智不小气,最重要的是,他很有爱国意识和责任感。
这些优势,让我最终顺利请到了他。
回去后,监狱里,那些警察依旧不依不饶,坚决不肯放出代表。
我和其他多名代表据理力争,终于得到一次交换机会——把我和其他代表换进去,而允忠则和在监狱里的学生代表出来。
法庭上,在绝对的民国法律的要求下,在龚律师唇枪舌剑的攻击下,权威和军阀终于做出退步,将我们全部释放。
但我没想到,龚律师竟然私下找到允忠,说要资助他留学,还说要把女儿许配给他。我看着允忠纠结神色,心思不免揪紧。
如我所料,赴法留学是他的心愿,他答应是人之常情,而他坚持独身主义,早先便立下一生为革命奋斗的誓言,所以并未答应张律师求娶他女儿的要求。
我那时还在想,他是我见过最洁身自好的男子,信仰志向都远非常人可比。
想到法国天气不怎么暖和,我又怕他一个人异国他乡难免受苦,珍而重之地织了一条围巾。
围巾是蔚蓝的海水颜色,我送到他手中时,他表情温柔的让人心动。
我也是回去之后才知道,当时社团里的一位学姐,也随他赴法留学。
我则继续留在此处学习,为当时的国家寻找新的可走之路。
但那时的国家是混乱的,无论是精神和现实,都被人牵着鼻子走。
我深知,要呼吁更多同胞,唤醒他们的觉醒意识。
每当我遇到瓶颈或者不被支持的时候,我就想起允忠。
我想和他通信交流,但想起他在那端繁忙的课业和工作,我又不忍心加重他的负担。
就在我焦躁不安的时候,大洋彼岸传来他的信件。
他在那端告诉我,他学习了共和的新思想,觉得比邻国的改革之路更为适合国家的现状。
我当时在国内也有所耳闻,听说京都已经有所行动,但并未大规模普及,说到底,还是上面有人压制的原因。
但这种现状不会持续很久,就像迷雾终归会被风吹散,只是需要一个契机。
3
战争爆发的很快,北方某些地方已经被蚕食。
允恩再次回国,是我和他通信的两年后。
彼时我已经顺利毕业,被组织调往南方工作,而他初回国,就调往北方某秘密党派,成为领头人。
我们从未见面。
但距离和时间并没阻拦我们相恋。
他在国外学习了新思想,被外国领袖坚持的革命爱情深深吸引,笑说原来以往的独身主义并不完全正确,世界上还有他向往的革命伴侣。
他向我坦明,他一直以为文十安是她心目中的革命伴侣,但后来发现不是,所以在短暂的恋爱过后,他转而向我频繁通信。
我被他的磊落说的脸红,他询问我是否准备好走完这条革命道路?
并且随他一起?
我现在犹还记得,我红着脸慢慢写下那些小诗的激动和幸福。
他和我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有坚定的信仰,我们的结合是因为爱情,却又不完全是为了爱情。
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为国家牺牲,不会阻拦对方在任何时候必要的赴义,也不会因为对方而轻易放弃这些信仰。
可我当时和姥姥住在一起,婚事需要求得她的同意。姥姥说,需要见到男方再说。
我便暂时将信件搁置,没有将心意表达出来。
直到他焦灼渴望的心情再次通过信件传到我手中,我才迫不及待地拾笔将心意说给他听。
4
革命路多艰险。
允恩回国后一直从事危险的革命工作,因为早年创办报纸、社团,很多人都认识他,这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尤其是党派在危亡之中艰难立足的时候。
我知晓这些,所在岗位也积极筹办各种反抗事宜。
但我们的关系,除了我们自己,并无其他人知晓,而我们各自的工作,也都没有像对方透露过。
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都心照不宣。
等允恩两年后,调到我所在的地方工作,我们才得以见面。
但繁忙的公务和迫在眉睫的起义活动,让他在新婚之前,甚至都抽不出空见我一面。
旁人若是知道,定要笑话我俩。
可我却不以为然,忙碌的难道只有他吗?
我自己不也是?
我赶到火车站的那天晚上,等了许久,也不见允恩来。
前后隔了数年时光,他的样子应该变了,而女大十八变,说不定他也认不出我来。
可我到了很晚很晚,也没见他来。
那怎么办呢?
我低笑着思忖了片刻,自己循着地址找到了他的住址。
那时还是上面安排给他的房子,屋子里布置的很喜庆,红色喜字,红色被褥,看得出来是我们的新房。
他的秘书远远的唤了声,“诶呦,怎么这么不讲理哟,哪有接新娘子用好多年前的照片的,这让谁认出来——”
我言笑晏晏地出现在他面前,秘书被我呆住,看了眼手中的黑白照片,激动地笑了。
那晚,允忠忙碌到很晚才回。
虽然隔了几年未见,但我们的心一直靠的很近。
交心,比身体的靠近更让人充实。
5
即使结婚,我们也是聚少离多。
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他回到家,有时我在忙,而我回到家,有时他在忙。
偶尔碰上,他刚刚拉上我的手,外面秘书就来喊他。我只能忍住泪水,亲亲他的脸颊,让他多加休息。
6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中,在他即将离家的那几天前,我发现自己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