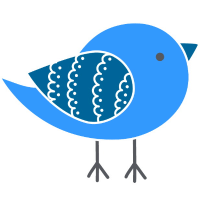深圳是座青春之城,梦想之都,是每天都有人爱着恨着、笑着哭着的都市大剧场。在一栋农民出租屋里,我曾认识一位女孩名叫桃花。十几年时光匆匆流逝,“人面不知何处,桃花依旧笑春风。”那朵美丽、热情、爽朗的桃花,是在风中微笑还是零落天涯?
在一个烈日似火的下午,我浑身臭汗,打着赤膊,搬家到福田区巴登街城中村一个四房两厅的一间小蜗居,9平方米。二房东杨姐租下来,把两个阳台和一个厅都隔成小房出租。
我大白天推门进去,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只有阳台上才有。我伸出手,可以轻松摘到对面阳台上挂着的衣服,这是农民村典型的“握手楼”。
适应了黑暗后,我看见一位身材苗条、长发飘飘的女孩,我朝她点点头,她嫣然一笑就进了自己的房间。那时我已成家,妻子怀孕了没有上班,后来从她唠嗑中我知道她的大致情况。她是湖南益阳人,12岁时父母双亡,老家还有一个大她两岁的精神不太正常的哥哥。
“东西南北中,发财去广东。”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响遍全国的顺口溜。她16岁闯广东的第一站是广州,在一家粤菜馆当服务员,包吃住每月400元。她个头高挑苗条,面若桃花,粉面含春拂杨柳,朱唇未启笑先闻。她是典型的湘妹子:性格爽朗,做事麻利,反应敏捷,很快在花丛中脱颖而出,翩翩起舞,自然而然就招蜂引蝶。
一家江苏建筑公司常驻广州办事处的老总常来这儿请客吃饭,他妻儿在老家,兜里有钱,便动了包二奶的歪心思。桃花刚从乡下来到花花世界,这么单纯的小姑娘,哪里经得住这种老猎人的哄骗?不知不觉就上了圈套。等她知道他有家有小,后悔了想抽身离开,却身不由己,她怀孕了。那是她心里最纯真的爱情的结晶,无论如何她非要生下来。这包工头一看大事不好,扔下一点给她堕胎的钱,彻底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她找到房东,准备按他身份证复印件上地址去找他算账。她有湘妹子的情深义重,更有一股惹火了就辣翻天的英雄无畏。她到派出所报案,一查是假身份证,Bp机也停了,至于上班具体公司地址和电话他从没告诉她。那时没有互联网,证件全是手造。况且这样的事在广州多如牛毛,也不算犯罪,每天飞车抢夺的案子都一堆,哪里查得过来?派出所几句话打发她走了,她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娘娘不听。
打掉了孩子,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心,她来到了深圳,在另一家粤菜大酒楼上班当迎宾小姐。
那时就业岗位稀缺,僧多粥少,人工便宜,是老板的黄金岁月,说一不二。稍微上档次的酒楼,门口都有几个模特儿一样的美女,我路过时只要看一眼,美女们必定朝我甜美地微笑着招呼:“老板,请进来喝茶啦。”桃花试用期工资500元,包吃住。可是穿着8厘米高跟鞋站十多个小时,楼上楼下招呼客人,她那虚弱的身体哪里挺得住?每天累得脸色惨白,一下班就虚脱倒在床上。老板一个月不到就炒她鱿鱼。

每一个孤身来闯深圳的人,都是一片浮萍,想要生存下来就得自寻渡口,自找归舟,狂风恶浪会把你带到哪里,那只能自求多福。她哀求老板让她多住几天,马上在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找了一家电子组装厂的流水线工作,试用期3个月,每月工资300元,包住不包吃,每班12小时。比起当迎宾小姐的唯一好处是可以坐着上班。
300元一个月工资,她自己再节约也没办法抚养在老家的精神不正常的哥哥,何况这点工资还经常拖欠。那时也有劳动法,除非闹出群体事件,基本上没有执行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当时的情境,也确实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就业和一大堆社会难题,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是中国当时参与世界竞争的最大比较优势。
几个月后,万般无奈之下,她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回头找到原来上班的那家酒楼,当时有位叫阿娇的迎宾小姐跟她聊得来。
那时揾工跳蹧实在太频繁了,老板说阿娇早就辞职,“嫁了”一个香港大款,回来吃过几次宵夜,一身珠光宝气,看得这些姐妹们眼睛放光,也妒火万丈。
桃花要到阿娇的call机,请她帮忙。没多久,一位香港货柜车司机“爱上”她,租下这个单间。我见过这位香港司机,才三十出头,脖子上戴着牛绳一般粗的黄澄澄的金链,斯文帅气,说话嘴巴上抹了蜜一样甜,经常从香港带些廉价但是时髦的化妆品、衣服回来。桃花陷进去了,做着甜蜜的等着嫁到香港去的美梦,怎么好意思跟人家谈多少钱一个月?那不成了买卖?她炒得一手好菜,学会了广东煲汤,两年为他堕了三次胎,桃花把他侍候得像公子、王孙一样。
桃花像《潇洒走一回》的歌中所唱: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可惜没有谁跟她用真情换一生,这位香港货柜司机只想潇洒走一回。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两年后他玩腻了,玩失踪了,再也没来过。昨天还如胶似漆,所爱的人猛然就消失,“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她大病一场,幸亏杨姐精心照顾,可是房租得交,在深圳谁活得都不容易。桃花开始去夜总会上班。有一天晚上九点多,我下班在村口碰到她浓装艳抹往前赶路,我哈哈一笑地打招呼:“这么晚了,你去哪儿玩啊?”她歪过头把我当成空气。
桃花其实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我儿子出生后,难免昼夜颠倒哭闹,想找一间公寓,她急忙说:“要不你们住我这间带阳台的,大很多,我住你们这间。你们搬家很累又多花钱,再说,住在这儿大家都熟悉,你在外面干活,我们可以帮忙照应,我可不是- -不是自己想省钱。”这话说到我心坎里。我那时是装修包工头,早出晚归,经常加班到夜半三更才能回来。桃花很喜欢我那胖嘟嘟的儿子,有空就抱去逗他玩。
不久她认识了一个姓王的台湾人。
那时台湾没有直通大陆航班,他都是经香港转机来回,深圳是必经之地。王先生祖籍浙江,四十出头,虽然是台湾土生土长,台湾腔调中依然夹杂着江浙口音,举止谦和,彬彬有礼,但从来没给过桃花礼物。她吸取教训,王先生每次来过夜,收400元,送一顿桃花做的美味的晚饭或者午餐。他如果住酒店带吃饭,也得花这么多。我有一次听到杨姐唠叨:“你怎么又怀孕打胎?你这傻丫头不要命了?”
桃花的哥哥也从乡下来闯深圳。他瘦高的个子,皮肤白晰,短直的头发中分,说话打招呼很清晰宏亮,是个精神小伙子,只是眼神有点怪异,看人时眼珠随着脑袋不停转动。他每天早上打好摩丝、穿着白衬衫红领带,提着人造革公文包,精神抖擞赶到安利公司参加直销培训,晚上回来时就在公用客厅、阳台上、甚至洗手间挥手大喊:“我来了,我,要成功!我一定成功!耶!……”
桃花有言在先,请大家多多包涵。同是天涯寻梦人,相逢何必相为难?
他在桃花的房间打地铺,每天吃饭、坐车、抽高档都要钱,而且被忽悠不断花钱买安利产品回来卖。从美容护肤品、洗涤剂、洗衣粉到纽崔莱保健品,在我们七户中慷慨激昂地推销,一问价格,贵得离谱,谁买?为了冲业绩升级,他照买不误。有天半夜,我见他扛上来一个长条形半人多高的大箱子,一问是安利净水器。桃花的房间很快堆满了,像街边的杂货铺。

桃花本就没存下钱,开始好言细语地劝他哥别再买,先把这些宝贝卖完。她不给钱,他就大吼大骂,接下来动手打,再接下来到厨房拿菜刀威胁。
客厅有一部电话,方便大家回复call机或对外联系,正常每人分摊20元足够。这个月杨姐去交话费,居然比上个月多20倍,她脸色煞白脚发料,打出清单核查,有好多夜半拔打的声讯台号码,收费每分钟一元多,每个时长都超过一小时。明显是桃花哥哥打的,可是没有确凿证据,她坚决否认,在深圳谈钱时,别谈感情啦。要我们全体租户分摊?小雷和小石叼看香烟嘻皮笑脸地说:“杨姐,我俩不可能多出一分的,除非你陪我们睡一晚。”
小雷和小石是江西抚州一个军工铀矿职工,初中毕业混了技校,然后下井挖矿。国家大裁军,他们工厂和矿山下马,呆在深山里无事可做,就来深圳了,没有稳定的职业,多数时候是安装监控摄像头。
那个月杨姐亏本了,她长叹一声:做什么生意都是风险。她只好把电话牵进自己的睡房,有需要用的进去打。
杨姐体态丰腴,穿着随意清凉,她常穿宽松衬衫和半截大头短裤,露出雪白的大腿和胳膊。桃花斯文地先敲门再进去,小雷和小石经常恶作剧,装着万分火急,闯进去回复call机,把杨姐吓得尖叫,有时她破口大骂。小石家是开个体餐馆的,他长得帅气,嘴滑皮厚,故意一脸不屑地调侃:“杨姐,我都不怕你占便宜,你叫什么鬼?外面人还以为你叫床呢!”大家哄堂大笑,杨姐也无可奈何。
深圳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奇迹发生。他俩那段时间还真做成了几单生意,开始胡吃海喝,买名牌服装,上夜总会。香烟档次从“白沙”换成“中华”。桃花从满脸嫌弃到含情脉脉,跟小石同进同出,比翼双飞。
桃花的哥哥熟悉场地后,越来越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家。厨房是公用的,他想吃就进去找,也不管是谁的,吃撑饱了才出来。我下班没有规律,他几次都把我的饭菜吃光了。桃花红着脸请我原谅,有一次炒了一大碗牛肉给我吃,又脆又嫩,又辣又香,真的好吃!
他脾气越来越暴躁,每天逼她拿钱创大业,不给就挥舞菜刀砍桌子劈门,她真怕了。有天早上她忍无可忍报警。十分钟后村治安员领着警察进来,一拥而上把他铐上要带走。
桃花忽然从房间冲出来,发疯似地抱着她哥哥,对警察说:“不,别抓他,我只是想吓唬一下他,他是我亲哥哥,头脑有时不清楚,你们别抓他!”她哭得撕心裂肺,杨姐和我们都作证。警察盘问几句,看看他神情后,严厉警告他不许拿刀动棍,然后摇头叹息走了。带回派出所又怎么处理他呢?那时的深圳治安和警察的压力极大。
亲眼看到目前这种状况,小雷和小石搬走了。我也胆颤心惊,她哥哥几次纠缠着我买安利产品,要发展我做他的下线,我都拒绝了。万一哪刻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呢?不久我也搬得远远的,再也没有见过桃花。
偶尔想起自己在深圳的青葱岁月,阵阵惆怅。哦,我的巴登街,我的邻居们,我的并末远逝的青春。
作者简介吕有德,1969年1月出生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现在定居深圳,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深圳有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