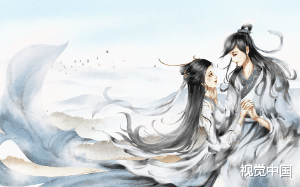城东废弃的城隍庙安静地伫立在江南微凉的细雨中。
我抱着墨梧剑沉默的靠在残破的庙像后,角落里轻薄的蛛丝网在风中禁不住地抖动。
脆弱,不堪一击。
雨声渐急,天色骤暗。我听到城隍庙外由远及近的杂乱的马蹄声,蓑衣摩擦的沙沙声被雨声掩盖得模糊起来。
糜烂的黄绸散乱在地,几株芜草搭在倒塌的落了红漆的折门上。
我的眼前渐渐晕开一幅江南古楼的画卷。在碧波淡墨山水交错之间,我隐约能看到……那女子温柔如水的眉眼。
一、
江南三月,柳絮纷飞,烟花盛开。
就在那年深春,皇帝病重。
太子未定,皇帝膝下六个儿子各怀心思,朝中势力表面一片风平浪静,但实则却是波涛暗涌。
皇后张氏是三皇子的生母,朝中大臣却多支持大皇子。
五皇子借口有疾在身想要避开朝廷争斗,却被六皇子揭发卖官鬻爵被拖下水。二皇子尚在边关戍边未归,六子之中唯一逍遥的只有四皇子李质。
朝野上下皆知四皇子李质爱花如痴,无心政治。曾经有大臣同他商议政事,结果等大臣把话讲完,却发现四皇子的注意力早就被一个挑着担子的花农给吸引了。
事后大臣责问于他,李质不仅不以为然,反而还觉得大臣说话太过无聊。
自此四皇子痴名远扬,再无大臣同他商议政事,他也乐的清闲,专心侍弄花草。
但我却知道,他平和温软的面孔之下,藏着一颗怎样缜密冷静的勃勃野心。
他小心的将它在人前收起,却在面对我的时候,毫无保留的将它展露出来,清楚的暗示着我已经处于他秘密的中心,除了全心全意为他做事到死,除此外再无逃脱的方法。
“本王要大哥的命。”
当他把玩着那枚白玉扳指漫不经心的对我下达命令的时候,我抱着墨梧剑站在屋子的另一边,看着窗外盛开的淡粉桃花默不作声。
他走到我身边,倚窗斜瞥着那开得热闹的枝头,薄唇抿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春意楼的红翘姑娘,也很喜欢赏桃花。”
“若不忙,便去看看。”
我看着桃花如是答道。
春意楼是京城有名的烟花之地,但我初见红翘,并不是在这里。
早在十年前,我还未遇上李质之时,便已认得她了。只是那时她并不叫红翘,而是叫一个更温柔些的名字——汀兰。
红翘是一个算不上美的女人。
虽然不美,但她却聪明温柔,善解人意。
她将我让进茶阁,小泥炉里的火舌轻舔着壶底,她拿着精致的绢扇,扇出一室清淡的梅子香。
我沉默的嗅着青梅秀气的香味,隔着飘飘袅袅的雾气看她。
她温柔的眉眼像被雾气染开了的水墨画,那画上的一笔一晕,都像是随着水的特性来描绘的。老天给了她一副好皮囊,却将她丢进了这红尘漫陌的青楼楚馆……不知是福还是祸。
“你同四皇子是何关系?”
我素来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明明是想问她的近况,却没料到开口便成了满含不明意味的质问。
她没并未回答我,只是扇着那泥炉,轻瞥了我一眼又垂下了眸。
之后便是一片静默,除了那壶中沸水煮开的声音外,再无其它。
我有些尴尬的瘫着脸,不动声色的抱紧了墨梧剑,心中暗自懊恼,打定主意不再说话。
“我替他收集情报,仅此而已。”
她用厚湿的巾帕裹住茶壶,用小钳子截了明火,只剩下暗红色的木炭还在滚烫的泥炉中闪烁。翻起两只浅沿的茶碗,她双手小心的捧起茶壶,让壶嘴微微倾斜。
我看着那壶嘴中倾倒出淡色的茶水,小小的青梅也随着水流冲进了茶碗,打了个圈,上下浮沉了几下便安静了下来,慢慢地沉到了碗底。
“大皇子的事——”
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恨不得把自己按在地上暴打一顿,明明想好了暂且不谈公事,却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还没有眉目,但李质既然让我同你配合,我定会全力相助。”红翘却并不介意,将茶壶重新放上了泥炉,“喝茶吧。”
我如蒙大赦,端起茶碗,也不顾碗中茶水滚烫便匆匆喝了一口。
茶水灼得我的口内都失去了知觉,但我却并未将茶水吐出。皱眉咽下去后,还要对红翘说:
“茶气清秀,好茶。”
红翘原本沉静的眸子里染上笑意,她下意识的抬起绢扇掩唇,而我却想看她微笑的样子。
“怎么,十年不见,如今竟然学会矜持了。”我捏住茶碗,心底暗自松了口气——总算没再说错话。
她闻言放下扇子,浅笑着嗔我一眼,那眼神中的万千风情让人陌生,我只能从她那微挑的眉梢中,依稀看出些她年少时的影子。
她说:
“妈妈夸我是幽谷的溪水,若不矜持,怎能成得了水?”
听完这一句,我忽然发觉她于我而言已十分陌生。
我说:
“但你不是从来不愿当水,宁可成灰,也不愿低头么?”
她脸上的笑容连同血色一齐褪去,怔在原地,一时之间没了言语。
二、
桃花将谢,江水东流。五皇子便在这桃花纷飞之时,以卖官之罪被皇上夺了封地,禁闭在家。
宫里的探子传来消息的时候,李质正在桃花林子里作画。
抱着墨梧剑站在他身边,我从来不知他有将蕙兰同桃花放在一起画的爱好,只是觉得那放在桃花树下的几盆兰花尤为碍眼。
又想到前几日见了红翘,但她已全然不似十年前的汀兰,这便越发看那几盆兰花碍眼起来。
趁着李质回房听消息的时候,我拿起搁在砚上的狼毫蘸了朱砂,将那株绘在画中的清丽墨兰全部涂红,这才缓了心中抑郁之气。
“本王从不知道,你拿剑的手,也能作画。”
李质扣着那枚白玉扳指站在我身后,我忙丢了笔,让开了位置。
“五弟的封地被父皇拿了,如今正坐在他的晋王府闭门思过。”他提笔在我未涂过的地方继续描绘,“审讯之时,有人提到六弟亦做过这等买卖,还拿出了条据,白纸黑字。”
他的笔尖微微一顿,忽而冷笑:
“真是好兄弟。”
他像是在讽刺五六皇子,但我却觉得那“兄弟”二字代表的不仅仅是那两个暂时失势的皇子。
“大皇子那里,你办的怎么样了?”他话锋一转,朝我看来。
“准备妥当。”
“三日之内,本王要听到大皇子薨天的消息。”
“尽力。”
风卷起沾着泥土的花瓣。
李质目光深沉的看我许久,忽然轻声问道:
“你可知本王为何要杀大皇子?”
他这目光太过渗人,我下意识地抱紧了墨梧剑,瘫着脸回他:
“不知。”
过巷的风吹走了那点残留的胭脂味,挂在檐角的铃铛发出一阵跳跃的碎响。
白日里的花街柳巷安静的就像空城一隅,只等夜晚把花灯点燃。
我去时,红翘还沉在睡梦中。
我本不想打扰她,但却禁不住以前养成的坏习惯,伸手夹住了她小巧的鼻子,不让她呼吸。
待她披头散发张牙舞爪地爬了起来,我拔腿就往暖阁外跑,却故意放慢脚步,让她追上来将我打一顿。
她果然扑了上来,借力冲倒了我后,便举起拳头一通乱打,全然不似前几次见面那样温柔如水,矜持有礼……与街上同邻里撕打的泼妇没什么区别。
我受着她的拳头,心底却十分高兴,试探着道:
“汀兰?”
她呼得往我头上来了一巴掌,瞪着杏眼低头看我:
“你这冤家!”
我登时欣喜若狂,像得了绝世宝贝一样,也顾不得她拍我的那一巴掌,伸手便搂住她的腰使劲摇晃:
“汀兰汀兰!”
她抬膝狠狠顶了我一膝盖,手忙脚乱地拉开我的手爬起来回房梳妆。
汀兰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女子。
不仅脾气暴躁,而且举止粗鲁,聪明滑头。
我初见她时,她正揣着一大包盗窃来的银子使劲儿跑,然后撞上了我。
白花花的银子如下雪般散了一地,引来一片混乱。
她先跑了,却把无辜的我推出去应付那追上来的失主。
那时还手无缚鸡之力的我被愤怒的失主打得窝在角落里咳血,若不是她半夜又突然出现将我带走,恐怕我也没有现在了。
而后她趁我病弱,威胁我签了一张卖身契。她不识字,那张卖身契……还是我亲自动手写的。
忍不住弯了弯嘴角,抬头,我便看到已梳妆好了的她打着哈欠从暖阁里出来。
散乱的乌发被一根普通的木簪挽起,未挽紧的发温柔的垂在她的肩上,身上只披了件蓝花褙子,露出里面月白色的里衣。她神色慵懒,看上去昏昏欲睡。
“李质下了命令?”她半张的眸底流过一缕精光。
我一下子有些分不清她到底是红翘还是汀兰。
“嗯,给了我三日期限。”我低声道。
她闭目摇了摇头,看上去渴睡得很。
我想问问她昨晚做了什么,但一想到此处是春意楼,而她正是楼里的青伶,那询问的话便生生堵在了我的喉中,吞吐不得。
“你可知当朝宰相徐尚儒?”她问。
我怎会不知。
这位徐大人就是当初让李质痴名远扬的无聊大臣,据说他那日被气的胡子乱翘,并扬言再也不和李质谈话。
但是七日之后,我却亲眼见他乘着素轿从府中后门进来,同李质一同秘密商议政事。
“徐公博学。”我只能这样说。
“不错,徐公博学,可惜教子无方。”她点点头,但脸上却浮起一抹讽刺的笑,“徐公在朝中属大皇子一派,经常聚在一起秘密商议政事。大皇子为人谨慎,平日里轻易不肯出门,只有这时……你才有下手的机会。”
“既然是秘密商议,又怎会让人知晓。”
“徐公之子徐婧容,很喜爱春意楼的阿甜姑娘,为了她,什么都愿意做。”
我紧盯着她泛着华光的黑眸,没有说话。
她似乎并不知道徐尚儒与李质的关系。
“明日,我便去问问阿甜姐姐。”她伸了个懒腰,扭了扭脖子,“若有消息,那檐角的铃铛便不取了,你尽管来就是。”
“……四皇子说此事需保密。”
“保密?”她轻嗤一声,纤指卷起一缕青丝把玩,半眯的杏眸里带着温软的朦胧,“春意楼的姑娘,哪个不是李质饲养的眼线?”
我一怔,一股淡淡的寒意悄然爬上我的脊背骨。
“那为什么……偏偏是我和你?”
红翘避开了我的眼睛,看向红雕窗外白蓝相溶的天,淡淡地道:
“谁知道呢。”
三、
第二日,那檐角铃铛并没挂上。
我站在青黛寒墙的小巷中,看着红翘从春意楼的破木门后鬼鬼祟祟的溜了出来。
她今日穿得格外素净,我一恍神,便好像看到了汀兰第一次穿裙子时别扭的拉扯着衣裳的模样。
只是那时她即便穿上女装也像个男子,而如今,却已长成真正的女子了。
“好不好看?”她见我恍神,便得意的拉着裙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
我言辞匮乏,笨嘴拙舌说不出一句漂亮的话,半晌只从嘴里蹦出两个字:
“好看。”
她看上去却似乎已十分满足,叽叽喳喳的说着些楼里姑娘们的趣事,虽然这些事都与我无关,但我却听得非常认真。
这是自我在春意楼见她以来,第一次看到她这般小姑娘的模样。
怎么看都看不够。
天不甚晴朗,许是昨夜落了雨的缘故。
她走在我前面,一边轻巧的避开发光的水沊,一边欢快的和我说着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我忽然便想起最初那句我欲问,却没有问出口的话。
“你这些年过的怎样?”
她蓦地停住脚步,我亦停住。
过巷的凉风拂动她略显肥大的衣裙,她回过头怔怔的看我半晌,忽而一笑:
“你问的迟了。”
她站在巷口,我站在巷中。
我忽然觉得,我与她不过是隔着两三步的距离,这一刻却仿若已隔了十年的春秋。
螺云寺在京城的西郊外。春末时节,山寺的桃花总是开的晚些。
我与红翘雇了辆马车,打算去螺云寺里看桃花。
她在摇晃的马车里吃着糖葫芦,我目不转睛的盯着她,生怕她一不小心就把竹签给戳自己嘴里。
她怀里还抱着两包花生,一袋麻花,贪吃的本性暴露无遗。
我第一次把墨梧剑背在了背上,只因手里要提一篮子临时买的香火,还得帮着拿红翘觉得好玩买的糖人。
马车摇晃的厉害,我终是忍不住去拉她的手:
“别在这儿吃,扎着自己怎么办?”
红翘灵巧的闪过,一双黑黑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以往的沉静模样尽数褪下,只剩下一个贪吃爱玩的小丫头,尽管她已不再是豆蔻年华。
“这样吃如何。”
她将竹签一横,像只花鼠一样啃了起来。恰好马车朝旁猛地一侧,她手没抓稳,糖葫芦敲在她脸上,刷地一下就蹭了半脸的糖。
她可怜兮兮的垂着头,嘴里还含着半块冰糖。我看着她狼狈的模样,忍不住笑了一下。
不知是不是许久没笑过的缘故,我弯起嘴角和眼角的时候,居然有些艰难。
她却举着糖葫芦直愣愣的看着我,惊讶的连脸上的糖迹都忘了擦。
“这些日子见你,总不见你笑,原来却是等着看我笑话!”
我刚要为自己辩解,却又听到她说:
“不过若是这样,让你多看几场笑话又何妨。”
眼眶蓦地一暖,我连忙闭上眼睛装作不在意地“嗯”了一声。却被一双微凉的手捧住了脸。
“喂,快看看我脸上还有糖没有?”
温热的气息带着冰糖甜滋滋的味道,轻轻地拂在我脸上。我不敢睁眼,却感到唇上慢慢覆上一层有温度的柔软。
像是河冰破裂,我清晰的听到心底传来“咔嚓”的脆响。
螺云寺建在螺云山山腰,我与红翘到山底时已经过了正午。
她走了没几步便说走不动了,宁可坐在地上打滚也不愿起来,全然忘记了是她自己倔着要来的。
我只得蹲下去让她爬上我的背,认命的背着她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