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紧绷的身体也稍有些放松下来。
她拨弄着梅枝,漫不经心地说:"还算你听话,这几年没往外乱说,不然当真要掘了你娘的坟,好叫她落个曝尸荒野的下场。"
我没说话,只是站在她身后。
这样的话,自从母亲死后,我不知听了多少回。
当年他们草草将我母亲下葬,又恐我嫁去孟府会将乔家腌攒事抖落出去,故而到现在也未曾告知过我母亲到底长眠何处。
我也曾派人打探,可始终没有结果。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忍着身上的不适问。乔宁绯冷笑一声,折断了梅枝,引得枝头雪落。
"你当真以为孟家当年是承情迎你进门?"
我皱眉不言语,只当她又要借什么话来挖苦我一番。
"孟大人当年新科进士夺了探花,却被逸朗公主相中,一旦做了驸马,便是前途未卜。娶你,不过是孟府权宜之计。"
"如今,孟大人官运畅通,逸朗公主殿下前些日已然去了他国和亲,你呢,自然要回到你该去的地方了。"
我脑中忽而浮现出这几日孟玄雁的冷漠,耳畔嗡嗡作响,脑中空白一片。
原来如此,原来只是一个拿来延长官运的倒霉蛋。
原来,是你已经厌弃了我。
"你呀,小时候生下来被父亲嫌弃,长大成婚了又被夫家抛弃,当真是可怜的紧呢。"
乔宁绯走过来紧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出最刺耳的话。
"父亲不喜你,孟大人也要离开你,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谁是爱你的呢?你娘?可她也……"
那时的我,已经被刺激的神志不清,也不知从哪里爆发的力气,抽出手狠狠一巴掌甩在了乔宁绯脸上,打得她后退一步摔倒在地。
我走上前,只想阻止她说下去,却未曾想到一个人影从一旁奔来一把推倒我。
11
我坐在雪地里,呆呆地看着孟玄雁将哭得梨花带雨的乔宁绯扶起来。
看着靠在孟玄雁怀中的她,我不由得怒火中烧,艰难地从雪地里爬起来想把乔宁绯扯出来。
手指刚要触碰到他们,孟玄雁喝止道:"乔宜尔!你闹够了吗!"
我一愣,随即只觉万蚁噬心,忍不住掉了泪。
我从来没看见这样的他,他从来也不会带着审视又警惕的眼神看着我。
反而,像极了我的那位所谓的父亲,护着乔宁绯转头斥责我的模样。
"阿姐,宁绯只是……只是想让你常回家看看父亲,我知道你不喜欢宁绯,可是父亲,父亲很想你……"
"你闭嘴!"我看着她的眼睛,恨不得生啖其血肉。
"呵,孟夫人果然性情彪悍,宁绯妹妹忧思你与家人关系不睦,你倒好,竟如此对她!"
"是啊是啊,早就听说这孟夫人阴郁非常,今日一见……"
"秉文兄,想来你在家,受制颇多啊哈哈哈哈。"
秉文,孟玄雁的字。
我转头看向说话的那群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却字字针对于我。
这时,乔宁绯在孟玄雁怀中哭着晕了过去。
孟玄雁横抱起她,没有再看我一眼,随众人径直出了梅林。
我表情空茫茫地看着他决绝的背影,双手却在袖中颤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仍由眼眶中的泪水滑落,沉重得喘不过气。
站了好一会,我才走出梅林准备回府。
"哎你们方才可瞧见了,孟大人抱着乔府二小姐往太医那去了。"
"瞧见了瞧见了,孟大人那模样,可担心得紧呢。"
"你们说的可是户部侍郎孟玄雁?可他的正妻是乔府大小姐啊!"
"快别说了,她过来了。"
我面无表情路过一群议论是非的贵女,只觉整个人像被冰水浇透。
"你们快瞧她那模样,头上那么多雪。"
"是啊,身上也脏兮兮的,不知在哪摸爬滚打,笑死人了。"
"你们声音快小些,莫被听了去……"
闻言,我顿住脚步,伸手从发间摸下一滩雪。镇定地走至一个角落,再难强装坚强,我蹲下掩面,紧咬住嘴唇,只求哭的声音小些,再小些。
"姐姐莫哭。"
我感到有人将厚实的大氅盖在我身上,抬头,泪水朦胧间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少年。
他生的爽朗适意,一身黑衣,扎着马尾舒眉浅笑着,俊美至极。
只是不知为何,眼中有些湿意。
虽骨缝疼痛,我也擦干眼泪勉强站起。
"多谢公子。"我微微一福,准备取下大氅离开。
他按住我放在大氅上的手,又替我掖得严实了些。
"姐姐当真不记得我?"
我这才抬头仔细端详他的脸,只觉少年下巴上的疤有些眼熟,却看不真切。
"夏叙,姐姐,我是夏叙。"他声音微微颤抖,伸手轻轻将我揽入怀中。
"叙儿,你……是你……"我再也难以忍受情绪,把头深深埋在少年的颈窝,发泄般的哭了出来。
很多年前,我随母亲从扬州上金陵寻找父亲,途中母亲捡到一个年幼的乞儿。
我母亲叫夏雯,便给他取名夏叙。
那年我十岁,夏叙只有六岁。
后来我们三个在乔府相依为命,直到府里来了人牙子,将十一岁的夏叙抱走。
我和母亲苦苦找了多年,都查不到线索。
12
我和夏叙走在回孟府的路上,已经是晚上,道路两旁积满了厚厚的雪,两个人踩雪的声音清脆,在寂静雪夜中很悦耳。
"那年我被拐至边境一户人家,没多久,敌军来犯,屠了整个村子,我躲在尸体下面才勉强躲过一劫。"
我皱眉,仍然心有余悸的看着他,当初那个瘦弱的小孩,已经变成了高大的年轻男人。
"后来,我被一位将军收留,做了士兵。也算是侥幸不死,久经战场,也博得了些名头。皇上亲征那年,我救驾有功,也拼了个将军出来。"
说完,年少的小将军笑着停下来。
"现在想来,定是阿娘在天有灵,保佑着我。"
我心中有些酸涩,伸手像小时候那样,拍了拍少年的头。
"我们小叙,最是厉害了。"
夏叙温顺的低下头,我却看见黑暗里他落了泪。
"阿姐,今日我回京便来寻你。在军营里我听说你过得很好,可为什么,阿姐今日哭的那样伤心。"
我一时哽咽,微微侧头不与他对视。
"阿姐自然过得极好的,只是今日不舒服。"
"姐姐撒谎。"他伸手将我拢在怀中。
"我回来了,再也没人敢欺负你,如若阿姐不喜欢孟府,我带阿姐走!我们去雍州,我能照顾好阿姐!"
我伸手回抱他,轻声安慰:"阿姐没事,你姐夫,对姐姐很好。"
"乔宜尔。"
听见这道冷冽的男声,我松开夏叙,惊讶地朝前方看去。
孟玄雁掌着灯,面色铁青。
夏叙冷笑一声,不动声色的挡在我面前。"这不是户部侍郎孟大人吗?找我阿姐何事?"
"阿姐?"孟玄雁笑一声,提灯走近。
"某竟不知,你这裴大将军的义子,竟是我妻的弟弟?"
他收敛了些笑意,多了几分清冷。
夏叙不甘示弱,亦上前一步。
"孟玄雁不知道的多了,不过连我阿姐有哪些亲人都不清不楚,我也敢问孟大人,这些年,究竟付出了几分真心!"
"好了,小叙,夜晚风大,快些回家去吧。"
害怕事情发展方向不由掌控,我上前拉了拉夏叙的衣袖,他却纹丝不动,双眼怒视着孟玄雁,似是要把他撕出个洞来。
我心中一暖,解下大氅披在他身上。
"阿姐答应你,有空就来找你,可好?"
夏叙拉着我,塞给了我一块玉珏,轻声:"姐姐,别让自己再被欺负了去,只管拿着它来找我。"
13
跟着孟玄雁回家的时候,我走在他前面,他在后面提着灯。
从前我未曾想过,跟孟玄雁待在一起会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情。
一路上两人都不说话,只是临近分别,孟玄雁问了句:"你未曾提过。"
我知道他在说夏叙。
轻笑一声,我回头:"大人不也没提过乔宁绯?"
他不言,把灯塞给了我,转头去了书房。
从踏雪寻梅宴回来后,我一连好几天觉得骨缝痛得钻心,额头上的伤现在还在流血。
我只觉怪异,就算是冬天,可伤口未免好得太慢了些。
又过了几日,那天早上我在作画,忽觉鼻腔中一股温热的液体流出。
鼻血淌在了我的宣纸上,好一会才止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终于那天,我叫来了大夫。
看见他欲言又止的模样,我屏退左右,他才幽幽开口。
"夫人,您这,恐怕是……血症。"
我瞳孔微微一震,险些喘不过气。
"当然,许是老夫医术不精,误诊也不一定。"
他没诊错,我去了好几个医馆,大夫都说我是血症,药石枉然。
我要死了,我心想。
阳光很好的一天。
我却枯坐在院中,四肢发冷,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城中大夫都说,我已经活不过三个月。
三个月,我在心中计算着。
现在已经是晚冬,我应该,还能活到夏天。
"乔宜尔,你在干什么?一连好几天都不吃不喝,别还没惩罚得了别人,先让自己遭了罪。"
声音从阁楼二楼传下来,我知道,是孟玄雁在那。
他在那待客,虽然我很想知道,为什么素来以不结交朋党闻名的他,近来也开始结党营私。
可我已经不想动了,我是想找人说说话,可不知道可以找谁。
夏叙么,他才回来知道母亲去世了,倘若又骤然得知阿姐也要去了,该多么伤心呢。
那,孟玄雁吗?
我苦笑着摇摇头,只怕,他正在计算什么时候将我赶出府去呢。
许是瞧见我这幅死气沉沉的样子碍眼,孟玄雁的声音已经带了温怒。
"来人,将夫人请回房去,既然她不想吃饭,那就把门锁好,什么时候她想吃饭了,再放她出来。"
14
我坐在床上,看向镜子里的自己。被关起来这段日子,我好像又瘦了不少。他们会按时送饭,可我吃不下,也不想开口说话。
只是在心底盘算着,怎样才能跟母亲葬在一起。
将母亲送我的陪嫁﹣﹣那根玉簪,还有她为我缝制的小枕儿当做我的陪葬吧。
思及此,我赶紧翻找出笔墨,记了下来。
可想想,虽然我这当了孟玄雁几年夫人,也算将府里打理的井然有条,可到头来,还是子然一身。
我睡在床上,做了个好生奇怪的梦。
我梦见,孟玄雁坐在我床边替我掖着被子。
他温柔地拍着我的背,像小时候母亲对我那样。
我在梦里笑了一声,嘟囔着:"才不是你呢,你只会像我的父亲。"
他伸手拨开我脸上散乱的头发,小声地说:"又瘦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锁了很久的房门已经打开了。
不知不觉,春天已经来了。
我躺在摇椅上晒太阳,夏叙在我旁边给我讲着边疆趣事。
我知道,他是在引我跟他一起去雍州。
很多树都发芽了,我看向孟玄雁书房的位置。
那里的小梨树,也准备迎来春天了。
只怕我,要永远留在今年了。
忽而抬眼,我看见了孟玄雁,他一身玄色长衫,身姿欣长,立在书房门口,他手上拿着一本书,正遥遥看来。
我避开眼,看向夏叙,继续听他絮絮叨叨。
日子一复一日过去,有阳光的时候,我就跟夏叙出去游游春,稍微冷些,就在屋中生起炉子,跟夏叙闲聊些幼中嬉闹之事。
后来夏叙临时接到任务,许久不曾露面。
我也就失去了乐趣,只是每日躺在摇椅上闭着眼享受人生最后的时光。
偶尔,我也会看见孟玄雁。
在书房门口的他,在阁楼待客的他,下朝回来又急匆匆出去的他。
我已经不像从前般在府门口等他,也不再没有自知之明地为他做各种食物。
偶尔见到他一个人,他总是用不明情绪的眼神看着我,我总觉得,那里面有一些悲伤。
而当他跟那些朋党走在一起时,他总会忽视我,不愿意看我。
我很想劝劝他。
秉文,别走那么快,不要负了一身清正。
15
可一日,府里格外热闹,我房中许多下人都被叫出去帮忙,等她们回来时,一个个面如死灰,比我这得了绝症的病人看着还死寂些。
我好奇地问:"怎的了。"
她们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回答。
直到我走出门看见府中定做的一箱箱的大红绸,才恍然大悟地跌在地上。
这府中,谁新婚才会有如此阵仗。
我握着红缎,泪流满面,鼻血顺流而下,将锦缎染得更红些。
我站起来擦干眼泪和鼻血,直奔孟玄雁的书房而去,身后有丫鬟哭喊着让我别去,可我已经一把推开了书房的门。
书房里有客,孟玄雁正在跟客人商量着什么。
偏头就看见我身前被染红的雪白衣裙和满脸泪痕,他怔了一下,疾走两步又停下。
他脸色苍白,唤来人:"把夫人带下去,如此这般成何体统。"
我从家侍手中挣脱,走上前两步,眼中是凄凉绝望。
"孟玄雁,你要和谁成婚?乔宁绯?"
他紧紧盯着我胸前一片血迹,张了张嘴,没有开口。
我心中立刻清明一片,他没否认,他要和乔宁绯成亲了。
我紧盯着他,逼上前去。
"父亲舍得让她做妾?还是说,你准备休了我?"
在一旁等待的客人听完不悦的说:"你还真是会想,乔二姑娘的母亲可是二皇子的姨母,乔二姑娘就是二皇子的表妹,岂是你这种下.贱腌攒货能比的?"
"住嘴!"
孟玄雁回头怒喝一声。
那人吃瘪,行了礼后匆匆走了,只是经过我时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认得说话这人,他是乔府的管家,乔宁绯亲娘谢雾音的人。
我看向书桌上那抹刺眼的红。
婚书。
"你受伤了?"
他沉默好一会才开口。
我突然觉得好累,太累了。
从前在乔府想方设法活着很累,后来到了孟府操持大小事务也很累。
现在为了孟玄雁,也很累。
"你给我一封休书罢。"
说完,不待他说话,我转身走了。只怕再不走,就会晕倒在他跟前。
即使那样,他也不会救我的,我想。
16
孟玄雁最终没有休弃我,他将我从正妻贬为了妾室。
正妻之位,是留给乔宁绯的。
我也从原本的院子里搬了出来,住进了西边的一个小院落。
以前跟着我的大部分人也被遣散去了别的院子,我将这些年的所有积蓄分给了她们。也算是不枉她们照顾我一场。
这个院子里没有那么多树,也看不到明媚的阳光,一点也没有春天的气息。
我想过走,可是孟玄雁派了很多人守在外面。
固若金汤,我却深感窒息。
我也没喝药了,本来喝药也没什么用,我现在,倒是恨不得早点死去。
这样也好下辈子早日做那自由的鸟儿去。有时一个人枯坐着,我也在复盘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
孟玄雁和乔宁绯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贬妻为妾,倒是本朝从未有过的先例。
他为了她,竟做到如此地步,想来,是真正的相爱了。
他是帝王的股肱之臣,在朝堂上从不站队,又是何时开始参与这些朋党之争。
从前听他说过,那些人,似乎跟二皇子有关。
似乎,逸朗公主去和亲,也是二皇子在暗中推泼助澜。
踏雪寻梅宴,二皇子。
乔宁绯也是二皇子的表妹。
想到这,我逐渐明了。
二皇子和七皇子一直为了储君之位在明争暗斗。
而逸朗公主和七皇子是一母所出,二皇子将公主送去和亲,无异断了七皇子一只臂膀。现在朝堂上的局势,显而易见已被二皇子全权握住。
这个时候谁还不会站队就是没有眼睛了。
我不由得苦笑,从前不相熟时,我钦慕孟玄雁,是因为他温润有礼,是谦谦君子。
后来我发现,他有一腔热忱,他清明,守得住底线,是难得的骨鲠之臣。
琉璃灯下,他温柔看着我,坚定地说:"宜尔,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官。"
孟秉文,你背离了本心。
17
这日下雨,我正在檐下练字。
孟玄雁来了,他撑着竹骨伞,在门口站了好一会才走进来。
我没管他,只是自顾自的写。
他垂眸看着我写,低声念:"一微尘里三千界,半刹那间八万春。"
然后失神好一会。
我有些不耐烦,停笔问道:"大人来做什么。"他从袖间掏出一个册子和一个印泥。
"乔世海要和你断绝父女关系,依照大梁律例,你和他要在这册子上签字画押,然后送往户部盖章。"
我倒也没有特别的反应,早已料到,父亲为了打破姐妹共侍一夫的流言蜚语,一定会这样做。
我接过册子,只是说:"可以,但劳烦大人帮我带句话,让他告诉我我母亲当年埋在了哪里,我要为我母亲迁坟,否则,我不答应。"
"可。"他应了声,又撑起伞走到雨中。
我静静看着从他伞上滴落的雨珠溅在地上,像一只只雨蝶。
莫名觉得这伞太眼熟了些。
"你觉着无聊,可以去花园走走,但不能出府。"
我牵强扯了扯嘴角,未免觉得荒唐。
"大人什么时候把外面的侍卫撤走,难道要关我一辈子吗?"
孟玄雁不答,只是还在自顾自的说:"宜尔,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微微侧头,狼狈的躲避了他的视线。
没时间了,孟玄雁。
不管是什么,都已经没有时间了。
乔世海果然动作快,不日就将我母亲埋骨之地说了出来,我也不带犹豫的在册子上签字画押。
现在,我已经不是金陵乔家女了。
我用玉珏去找过夏叙,可他不在家,他还没回来吗…
我有点失望,如果母亲知道是我和夏叙一同葬的她,她会很高兴。
虽然我银钱不多,可好在风水先生并没有要我一分钱,此外,他自己还叫来了负责迁坟的人。
我觉得他跟孟玄雁派来跟着我的人眉来眼去的,像在交流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看着母亲新坟旁边的空地,很好,我很满意。
以后,我就跟母亲一起长眠此处吧,这里山水清秀,下辈子,一定能投个好胎。
18
外面疾风骤雨,我躺在床上,刚刚才止住鼻血,现在睡也睡不着,只觉得今夜这风刮得太大了些,我头上的瓦片都在卡啦作响。
不时,有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来,我倏尔坐起。
是夏叙,他回来了。
少年浑身湿透,双眸通红,他走上前想抱抱我,又停住手,无奈的笑。
"我怕惹湿了阿姐的衣裳,"
我毫不在意,踮起脚抱了抱他,问:"你这几日去哪里了,我寻不到你,只得先将阿娘葬了。"
他拉着我坐下,将一切细细讲来。
一番说道,大抵就是朝堂上有人私通外敌,卖了许多军中情报,导致七皇子在边境节节败退。他被义父裴大将军派去秘密探查,却只查到些皮毛。
我摸了摸他的头,轻声安慰。
他抬起头,一双泛红的眼眸死死看着我。
"孟玄雁把你贬成妾去娶那娘希匹的乔宁绯,当真是有眼无珠的蠢物。"
说完他抽刀站起来就要往外冲。
"看我不宰了他这斯!"
我使出全身力气才堪堪拉住他。
抱着他精瘦的腰,我说:"姐姐跟你走。"
他终于顿住,惊喜的转过身。
"此话当真?"
我松开他,无奈地用手点了点他的额头。
"跟个孩子似的,你总要给我一些时间处理好身边的事吧。"
他挠挠头笑起来说:"姐姐,我们去雍州,你会喜欢那里的。"
我跟夏叙约好五日后由他来接我。
届时也是他和裴大将军的军队返回雍州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什么好收拾的,我孤身一人来孟家,这几年不曾生育,走的时候自然也是子然一身。
我推开窗,看向夜空。
雨已经停了,头上也出现了月亮。
我趴在窗边看了好一会,才发现不远处孟玄雁也在,他也在抬头看月亮,只是他忽然转头,与我刚好对视。
那一双眼,孤单又隐忍。
我也一时间看不透了,只当他是路过,冲他微微一福,我起身关上了窗。
19
与夏叙约好的日子就是明天。
这几日一连几天都是好天气,我都有些不舍离去了。
孟玄雁在上朝还没回来,我来到他书房外,拿着铁锹,在小梨树下面铲着,我身体不好,挖了一会就要歇息好一会。
直到孟玄雁下朝回来,我才将几年前埋下去的,我和孟玄雁一起酿的梨花白挖出来。
孟玄雁站在晦暗不明处,我冲他晃了晃手中的酒罐,露出了这么久以来最开怀的笑。
我们两个坐在书房里,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这么平静的坐着聊天。
我为他倒了一小杯酒,轻笑道:"大人可还记得这酒。"
他举起来抿了口,才缓缓说:"这是那年你我共同酿做的,不是说要留给女……"
他顿了顿,似是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我也小口品着,接过他的话:"说要留给我们女儿出嫁的时候喝。"
"大人这些年,其实待我很好。"我放下酒杯,认真的看着他。
孟玄雁不自觉紧紧捏住酒杯,直到关节泛白。
"我知道,我是金陵最没有家教教养的闺中女儿。"
"大人高风亮节,品行端正,古今之道皆在大人心中。大人是这金陵,最好的男子。"
"就算是被逼着娶了我这不入流的妻子,大人以前也从未对我说过一句重话,从来都是对我有求必应,以礼相待。"
"大人教我习字断句,教我琴棋书画,我嫁过来时不足十七,还不会管理府中大小事务,大人你一边耐心教我,一边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深夜。大人说是我的恩师也不为过。"
"宜尔从前做过许多错事,此番知晓大人心有所属,更是自觉难堪。"
"大人是我的恩人,你给的,宜尔无以为报。只求大人能不计前嫌,放宜尔离开。"说到此处,孟玄雁面色似是有些苍白。
"不能。"他垂眸,我看不到他的情绪。一时间,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我一杯一杯小口喝着,他在一旁看着我喝。
忽然听见他笑,我不解的看向他。
他温柔地看向我,说:"只是突然想起,有一次你吃完酒犯浑,非说我是马,让我背你。"
我也回想起来,似是有这么一回事:"那您背了吗?"
他干咳一声:"自然……没有。"
我偷笑,其实我记得。
那是定北侯的宴席,高门贵女都不屑与我相处,我一个人坐在角落喝闷酒。
我平素沉稳,只是吃完酒后总做一些无理取闹之事。
回家路上我对着孟玄雁一会叫娘一会又说他是马,我说我不要坐马车我要骑马不然就不走了,说着就要往窗外跳下去。
孟玄雁拦腰抱住我,黑着脸走下马车,将我背在他背上。
一边走一边训斥我下次不要让我喝那么多。
那时候我其实已经有些清醒,却骑马难下不得不装糊涂。
两个人的影子被月光拉得老长,我被他背得稳当,他叹了口气说:"宜尔,以后不要一个人黯然神伤了。"
孟玄雁似是彻底放松了下来,他又笑着说:"昨年我因谏言被皇上杖责,被抬回来的时候你哭得跟个小兔子似的。我起夜的时候,看见过你在哭着扎皇上小人……"
我赶紧起身一把捂住他的嘴,紧咬牙关:"这你也说,不要命啦?"
他又低低笑起来。
那些实在是太久远又美好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只觉如在梦中。
我笑了笑,又跟孟玄雁提了许多我们两个的趣事。
他也笑着同我一起回忆。
原来很多事,他都记得。
现在的他,像极了从前。只是我知道,明早,他就会恢复那样冷淡的模样。
两个人说说笑笑,不觉间一坛酒已经见底。他送我回到房门,道别后转身欲离去。
我扶着门,忍着心中酸涩叫住他:"秉文。"
年轻的男人回头,我隐约能看见他脸上醉酒后的红晕。
"秉文,朝堂之上波谲云诡,万不可行差踏错。我知你一生刚正,又敬你舍掉这一身清誉,甘愿去做那背负骂名之人。"
"宜尔不怨大人,祝大人此行圆满,往后一生无波无澜。"
借着光的昏暗,我没能忍住落泪,最终关上了门。
我靠着门滑坐在地,用力忍住哭腔,感受着那个人将手轻轻放在门上。
"懂我者,宜尔也。"
20
第二天,在夏叙的帮助下,我顺利逃出了孟府。
站在街角,我又看向曾经无数次等待孟玄雁回家的门口。
转头释然笑了。
坐在出城的马车上,我心绪不宁,思忖着如何告知夏叙我命不久矣的消息。
可夏撩起车帷看了一眼,又催促前面的马夫走快些。
我疑惑,想探头朝窗外看去,一只筋骨分明的手掌就将我眼睛盖住。
"姐姐,别看。"
我瞬间懂了,是……他吧。
可为了方便出城,夏叙本就走的人流较少的城东,这却让孟玄雁打着快马很快就将我们截住。
"吁!"
夏叙听后冷笑一声,抽了刀就跳下了马车。
我害怕两人冲突,也紧随其后。
孟玄雁冷着脸跳下马,朝我走过来。夏叙拿刀拦住了他,我急忙制止,将夏叙挡在身后。
"你要走?我以为,你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意。"孟玄雁目光越过夏叙,直直地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他还穿着官服,只是策马狂奔时乱了衣襟。
"阿姐莫要与他游说太多,待我砍下这狗官首级为你消气。"
我偏头低喝:"夏叙,他不是,莫要胡来!"
"阿姐,为何?现在全金陵都知道他是个贬妻为妾的狡诈小人,到现在你还要护着他么!"
夏叙气得重重丢了刀。
我深吸一口气,劝慰:"你先过去,这是姐姐的事情。"
夏叙冲孟玄雁冷哼一声,提刀上了马车撒气。
我这才缓缓转身:"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会让你的计划功亏一篑。"
"那又如何,难道要我不来寻你,眼看着你离我而去么?"
孟玄雁看着我,双眼泛红。
"孟玄雁,你喜欢我吧?"我笑。
他抿了抿唇。
"我爱慕你。"
"玄雁,我要去雍州,在那里有夏叙护着,我会很安全。"
孟玄雁气急,逼近几步:"那你何时回来?还是你不会再回来了?"
"我会回来,几个月之后吧。"
只是那个时候,我是被送回来安葬的。
"对不起,我不该不和你商量这件事。要拔掉二皇子这根毒刺,只有找出他通敌的证据,而他所有命令,都是通过他的姨夫,也就是你的父亲乔世海传达的。"
我走上前,像平常一样为他正了正衣襟。
"我知道,你是朝堂上最为刚直的人,只有你真心做了乔宁绯的丈夫,才能彻底取得乔世海信任。"
孟玄雁握住我的手吻了吻。
"七皇子与我商议时,我本不欲。可他说覆巢之下无完卵,二皇子迟早有一日玩火自焚,届时乔家必是抄家灭族的重罪,连你也躲不过。"
"所以你,劝说乔世海与我断绝关系?"我柔声问。
他抱住了我,将头搁在我的颈窝,闷声"嗯"了一句。
"我只有表现出不喜欢你的样子,他们,才会信我。这是一场生死未定的赌局,你若知道了,必然卷入其中,若我失败,你也难逃一死。唯有将你摘出去,届时,我若成功便好,若是失败,也不会牵连你。"
我轻轻推开他:"你既做了这么多,过几日就要和乔宁绯完婚,正是关键时候,切莫掉以轻心,我只是……去雍州散散心,等你成功那天,我就会回来,可好?"
正当他踌躇着,突然有人认出了他,正是那日在府中嘲笑我摔倒那位贵公子。
转身进了马车,夏叙此时也催促着车夫赶紧走。
车轮滚动间,我从车帷缝中最后看了孟玄雁一眼。
他长身玉立,与我遥遥相望。
突然想起来新婚那夜,他也是这般无措的站着,离我很远,我也从盖头缝中窥探即将与我相濡以沫的丈夫。
那时的我们绝对想不到,此生诀别,还是这相似的场面。
再见啦,孟大人。
21
去雍州路上。
"姐姐,孟大人方才说的……可是真的?"夏叙摸着鼻梁,略略尴尬的开口。
我挑眉:"你都听见了?"
他尬笑:"这,我们习武之人,耳朵自然比旁人好使些。"
我拍了拍他的头:"那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他狗官啦,他是个一顶一的好官。"
"可他眼睁睁看着你被欺负!还把你关在后院,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我失笑,脑海中浮现出摔倒那日和书房争执那日他想要走上前却不得不停止的脚步。有些事,当真是不由己。
也许是雍州比较适合我吧,我居然在那里比预想的多活了一个月。
油尽灯枯那日,夏叙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他说,孟玄雁做到了,二皇子下了狱,不日就要被贬去蛮荒之地,乔家满门抄斩。
我笑了笑:"小叙,阿姐想娘了。"
"阿姐,你别走,小叙不想再失去阿姐了,阿姐……"
我吐了口血,脑中却浮现出一个人的影子。
他在书房里挥毫,在荷花池边作画,他心疼地看着我被烫伤的手,一口吃下我做失败的新菜,我看见他明明脸色突然变得比菜还绿,却称赞中我做菜真好吃。
我看见他在宴席上与一群女眷针锋相对,只因为她们排挤我,说我不知礼数。
他教我工巧之术,我造出来的第一把伞就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对不起,孟玄雁,是我失言。"
番外
我走在灰蒙蒙的路上,四周哭声一片。
"姑娘,你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死了?"
我默然,这人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又不是真想死。
站在桥上,什么也看不清。
我双手托腮,正想着阿娘会在哪呢。
一声没好气的声音响起来:"乔宜尔。"
我惊讶的转头看去。
孟玄雁正撑着伞,站在离我不远处:"小骗子,你可真难找。"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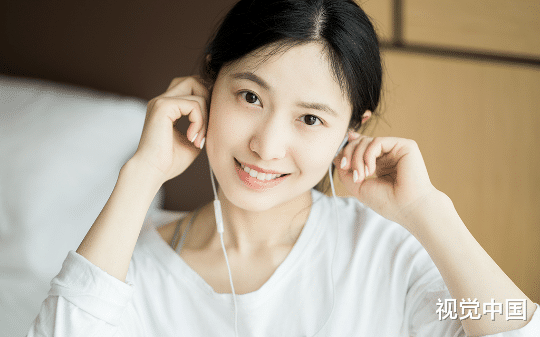




那人也死了?[得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