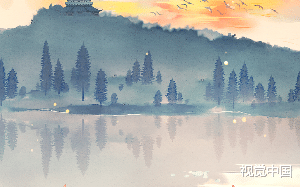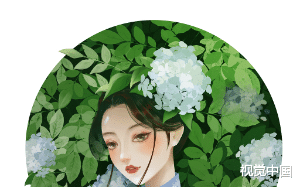文章转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即删作者:蒜泥小秃头
我夫君晏挺之在外惹了桩风月。
对方是个四品官家的嫡女尹清月,已怀孕三月。
说是别无所求,只求腹中血脉能有个名分,入晏家的族谱。
我与晏挺之成婚三年,一直沉醉于金石学研究,未曾有孕。
婆母听闻尹家嫡女有孕,要纳尹家女入府,生子便可抬为平妻。
而前些时日,我父亲刚因反对新政被罢官流放,失了宰相之位。
一夕之间,我从原本人人羡慕的京城第一贵女,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尹家女月份渐大,晏挺之不得不来求我,等我松口才好迎她入门。
「姝妤,我心里从来都只有你一个,清月即便有子嗣,也断不会越了你的次序。」
我将长袖从晏挺之手中抽出来,毫不避讳地直视着他。
「晏挺之,我们和离吧。」

图源网络 侵权删除
1
我叫宗姝妤,是人人称道的京城第一贵女。
我父亲宗韩非是状元出身,后官拜观文殿大学士,一朝宰相。
母亲王氏为镇国公独女,极为看重我的教育,给了我不输哥哥的悉心栽培。
我七岁拜大梁女词人玄安为师,十二岁一首婉约清丽的咏棠词让我名冠盛京。
十五岁那年,北靖王想要娶我为妃,母亲气得不轻。
她嫌北靖王风流成性,家中姬妾成群,实非良婿。
况且,上嫁吞针。
宰相府风光已极,父母不愿我入公侯王府,浪费似水华年与人缠斗。
父亲以想多留我两年为由,婉拒了北靖王。
那年,晏父官至参政,为我父亲的得力助手。
其独子晏挺之高中进士,清逸俊朗,为人谦逊,颇有我父亲当年的风采。
晏家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却也算得上满门清流,家风严谨。
母亲说,嫁入这样的人家虽不是最风光,却少了高门婆母立规矩、摆脸色;没有世族大家的妯娌间攀比炫耀,最是舒心。
晏挺之许我一生一世一双人,此生绝不纳妾,抑或豢养外室。
就这样,十六岁的我嫁给了晏挺之。
我和他都酷爱金石学,兴趣相投。
饮酒咏棠、泛舟赏月、赌书泼茶,度过了胜似蜜甜的三年。
直到朝中有改革派施行新政,我父亲反对,被官家革职、流放瓜州。
公公见风使舵,强烈抨击我父亲,宣布支持新政,迅速赢得了官家的信任,继任了宰相一职。
他登上宰相之位之后,立刻调任晏挺之为洛阳府尹。
我正因父亲被罢官,心绪凄迷之际,晏挺之却从洛阳带回来怀孕三月有余的女子。
在外,晏父与宗家割席,避之不及。
在内,婆母许诺怀孕的尹清月生子便可抬为平妻。
虽然明面上不说,这一家人的所作所为,已有断我在晏家的根基之意。
「只有母族的强盛,才能抑制人性的低劣。」
从前母亲将我护得太好,我一直不懂她此话的深意。
如今懂了,也被伤透了。
尹家女月份渐大。
晏挺之不得不来求我,等我松口才好迎她入门。
「姝妤,我心里从来都只有你一个,清月即便有子嗣,也断不会越了你的次序。」
我将长袖从晏挺之手中轻抽出来,毫不避讳地直视着他。
「晏挺之,我们和离吧。」
2
晏挺之瞪大了双眼,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姝妤,你说什么?」
「尹清月原也是官家女,当得起你这宰相府的当家主母。」
「她如今有孕,你别委屈了人家,我给她倒地方,我们和离。」
晏挺之微垂了下眼。
手中捏紧了质地上乘的琥珀茶盏。
那茶盏还是我们一同在汝州淘来的。
「姝妤,你我成婚三年,相约白首,胜似蜜甜,我绝不同意与你和离。」
相约白首,胜似蜜甜?
我心中冷笑。
却不愿与晏挺之多费唇舌。
我让丫鬟雨玲拿来了我拟好的《放妻书》。
在晏挺之面前徐徐展开。
「挺之,如今我父亲被流放,母亲病重,家中需要我照顾。你眼下有了新人,日后还会有孩子,我们不如解冤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晏挺之惊愕地看着我。
「你这是在怪晏家凉薄,寡恩薄义?姝妤,现在朝中什么局势,你不是不知道,若我父亲展露出对岳父大人的一丝同情,晏家便会被改革派攀咬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明哲保身与落井下石终是云泥之别,他晏家怎会不知?
我幽幽地抬眸看他,慢声慢语。
「你父亲如今位高权重,我怎敢议论?」
晏挺之自知理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提笔蘸墨,将和离书递给了他。
「和离我只要我带来的那份嫁妆,其余别无所求。」
「我说过,我不会与你和离。」晏挺之甩开衣袖,态度坚决。
我放下了毛笔,看着香炉里升起的一缕缕透白的香烟,静下心来。
「若不和离,我便只好去报官了。」
「你说什么?」
晏挺之皱眉。
「宫里的贵太妃薨了,此是国丧,晏家叔伯的儿媳去世,这是家丧。」
「你背着家国两重丧,暗自与尹清月苟合,搞大了她的肚子,若论礼法,该当何罪?」
晏家如今权势滔天,若是报官,他们也是不怕的。
只是这世代清流的美名,怕是完了。
「姝妤,我知你素来温婉柔和,没想到,你居然……这般铁石心肠。」
女子只要是做符合男子利益的事,便会被他们冠上各种美名。
贤良淑德、温婉大气、隐忍柔和。
一旦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便是心狠手辣、铁石心肠、蛇蝎妇人了。
晏挺之压低了眉看我,似是关心。
「姝妤,你有没有想过,与我和离,满京城的人会怎么说你?」
我笑了笑。
「左不过说是你晏挺之的下堂妻罢了。」
「我又不需要在晏家讨一杯残羹冷炙,要什么徒有其表的贤名?」
我拿着和离书走出晏家的那天。
轰动了整个京城。
有人笑我傻。
晏家如今风光无两,我就这么长此以往地熬下去,即便真不能生,也不要紧,拢几个小妾生的孩子到自己手里养,总会熬出头的。
有人叹我痴。
这世上哪有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像我父母那般琴瑟和鸣的夫妻,只羡鸳鸯不羡仙罢了。
但我离开晏家浩浩荡荡的队伍还是再度震惊了他们一番。
京营节度使宗格非为我兄长,他亲自来晏家迎我回宗府。
十个嬷嬷、二十个丫鬟、四十个小厮、队伍绵延十里不绝,盛况一如当年。
也有人后知后觉击节赞叹。
宗家大小姐和离。
可不是刚好给重振宗家带回了救命钱?
3
兄长愤怒于晏家一朝得志,两面三刀,更是愧疚于他护不住我,自责不已。
我整理着这些年收藏的文玩字画,语气平淡。
「哥哥,你与父亲母亲给我的已经够多了。」
「这人世间的路,终究不能由你们代我走,要我自己走下去。」
「若我遇上了风浪,不能珍重自身,重振宗家门楣,倒是白白枉费了你们对我的一番心血,这辈子便无生趣了。」
兄长像是重新认识了我一般,心疼又欣慰地点了点头。
我给母亲请了太医来看,日夜在她床前侍奉。
待母亲精神好些时,我已将宗府的下人们放出去一批,削减家中各项开支。
又把园子里的地分包给各院管事的嬷嬷们,让她们自产自销,将盈余的一半上交给府里即可。如此一来,等于变相地给她们涨了月银,免了她们见宗家败落,人浮于事,生出可丁可卯的做事态度。
宗府所用花草蔬果,亦无须在外采买,节省了一大笔银两。
母亲的病痊愈后,我已与父亲通信数日。
告诉了他我即将带着家仆去瓜州的消息。
【家中有姝妤在,唯愿父亲心安。】
每封信的结尾,我都会执笔添上这么一句话。
朝中局势变化莫测,官家天意难以揣度。
父亲被流放,可兄长仍任京营节度使,手握军权,宗家仍有一息尚存。
正待我和各院掌事嬷嬷们核对账目时,宗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怀孕三月半的官家小姐尹清月。
「她怎么还有脸来我们宗府?什么不知羞耻的下流东西,就该叉出去!」
雨玲愤愤不平地说道。
我看了眼雨玲:「是我平日里纵得你越发没规矩了。」
她适才住口,嘟囔了句:「我就是替小姐鸣不平嘛。」
雨玲年纪尚小,看不懂男女之间的那些弯弯绕绕。
以为男子变心,必是另一女子勾引的结果,其实不然。
破坏我与晏挺之这桩婚的罪魁祸首,从来都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他一时升了洛阳府尹,便得意忘形了。
即便没有尹清月,也会有江清月、风清月、柳清月。
我请了尹清月进宗府客厅,唤下人给她上茶。
她这些时日确实也不好过。
自从我与晏挺之和离之后,京中有关她与晏挺之孝期苟合的传闻便再也掩不住了。
眼见她月份越来越大,可晏挺之就是不肯迎她入门,连做妾都没有指望。
毕竟宗家如今落败,晏挺之惹出风月,逼走发妻的名声实在不好听。
尹清月父亲是太晟府大司乐,已经因此事丢尽了颜面,闭门不出了。
「晏夫人,不知今日登门有何贵干?」
听我唤她晏夫人。
尹清月脸上顿时挂不住了。
「姝妤姐姐,你真是折煞清月了。」
她在我身前低头福礼,一支斜插的翠玉步摇映得她冰肌玉骨,眉眼如画。
真真是我见犹怜。
「姝妤姐姐,你在挺之心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他唯一的妻。我原也是个外人,日后,只求能侍奉你与挺之左右,绝不会痴心妄想。」
「就请姐姐大人有大量,回到晏府吧。」
我沉静地看向尹清月,这才明白她段位有多高,自不是我能比的。
她身上有孕,我更怕磕碰了她,坏了我宗家百年清誉。
我只好虚与委蛇,让雨玲扶她坐下。
「我已与晏挺之和离,于他已是过去式。」
「尹小姐凤栖梧桐,若来日诞下麟儿,前途必不可限量。」
演完这出戏,她也可回去跟晏挺之交差了。
送走了尹清月,我让雨玲拿来我藏的龙脑香,打开门窗,熏一熏这客厅里的污浊气息。
花自飘零水自流。
有些心里的刺。
终是横亘在我与晏挺之之间,无可消弭。
我备好行装启程去瓜州那日,晏挺之站在宗府门口等我。
他相貌堂堂,儒雅风流,如今又位高权重,比以往多了几分贵胄气度。
众人面前,他做足了求和的姿态,低头靠近我。
「姝妤,一切都是我的错。」
「那孩子生下来,就放在我母亲房里养着,我此生不纳任何人进晏府,你跟我回去好吗?」
我躲开了晏挺之,雨玲为我披上披风。
我平淡地看向他。
「挺之,其实,你不是不懂,女子立于世的艰难处境。」
「你只是在赌。」
「赌一个女子无法承受离开夫家的惨烈代价。」
「赌一个女子无力抵御外界的流言蜚语。」
「赌一个女子不敢挑战这千百年来定下的男尊女卑的规则。」
我身体微微颤动,眼眸轻沾泪意。
「可你忘了,我亦是好赌之人,从不轻易认输认命。」
晏挺之抿了抿嘴唇,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被雨玲扶着上了马车。
车轮渐渐驶离。
盛京的人与事,从此不再留恋。
4
瓜州崇山峻岭、烟瘴遍地。
行路越艰难,我心中为父亲的担忧就越多。
他常年在权力中心,位高权重,一朝狠狠跌落。
只怕万关好过,唯心中那关难过。
来之前,我已让管家在服役地近处置办好了一座宅邸。
一到了瓜州便使银子打点好了狱卒,接父亲到雪庐一叙。
看着曾经丰神俊朗的父亲,变得沧桑憔悴,两鬓斑白,我心中的苦痛难以名状。
我吩咐下人们替父亲沐浴更衣。
而后,我亲自为父亲梳栉,重整衣冠。
「姝儿,是为父当初看走了眼,为你挑中了晏挺之,真是害苦了你……」
我坦然一笑。
「父亲,姝儿离开晏家,如久陷樊笼之鸟,复得自然。」
「又何来您害苦了我之说呢?」
「况且,这世上绝大多数事,不到最后,都不知道是喜是悲、是祸是福。」
「只要父亲安好,就不怕我宗家没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我看着铜镜中父亲的眼,终于有了些许曾经的光芒,心已大安。
深夜,月色似练。
我独自在院内饮酒,享受着久未有过的平静,却总觉得雪庐里少了些什么。
想起宗府院子里那大片的海棠花,便让雨玲栽数十余株海棠树来。
次日清早,下人们正前前后后忙着,管家走进堂内跟我说:
「小姐,门外有一队车马。」
「来报的小厮说,他家公子路遇瓜州,发了寒症,想借一地方休息。」
雨玲听了不满道:「什么脏臭的男人也妄想住进雪庐?瓜州是没有别的客栈了吗?」
管家笑了笑。
「说是看到我们院内栽种的海棠极好,想必家主是有惜花之情的雅士。」
我思忖片刻。
瓜州为穷乡僻壤,寸草不生。
这若是有适宜居住的客栈,我也断不会在这置办宅邸。
雪庐一共有两个院子,我住东院,起居与会客在中堂,平日里与外人根本碰不上。
「忠伯,把西院收拾出来给他们住吧。」
「再让陆郎中给那位公子诊治,别怠慢了。」
「好。」
三五日过后,我便将这件事抛诸脑后了。
我每隔一日去探望一次父亲,给他送去小厨房里精心烹饪的菜品。
亦将京中可拆卸的势力跟父亲讨教。
余下时日,我将之前在安阳殷墟出土的一百三十二片甲骨卜辞,归置、收录、完完整整地载入《金石录》里。
晏家虽不是钟鸣鼎食之家,可晨昏定省、亲戚走动、后宅纷争一样也不少。
我事必躬亲,精力心血不过是被两厢拉扯。
三年间,竟鲜少有这样大段不被打扰、专心著书的时光。
此时此刻,风吹海棠,花如雨落。
我让雨玲拿来了我的古琴素问,坐在海棠树下饮酒弹琴。
幽幽琴声在我指尖婉转流泻。
我闭上双眼,只闻暗香浮动,这才是记忆中应有的早春。
诗意、酒意,以及未被人辜负的海棠春色,都在当下。
我亦可把心中的苦,都酿成甜。
弹到曲子的下阕,耳边却传来了清雅至极的笛声。
那笛声清脆悠扬,如同山涧清冽碧透的溪水,沁人心脾。
琴声与笛声交融缠绕,竟仿佛我早已认识了那笛声的主人,心意相通。
全天下笛子吹得这样好的,唯有一人。
那人在大梁,音画双绝,久负盛名。
宗家如今落难。
我流言蜚语缠身,不愿再招惹任何是非。
思及此。
我立刻抚平了琴弦。
琴声戛然而止,笛声也带着惆怅一般,因此渐微。
「小姐,你怎么不弹了?」
「倦了。」
「多雅的笛声啊,也不知西院住着怎样一位谪仙。」
雨玲憧憬地说道,我嘱咐她不要妄言。
便起身回到书房内。
关上了门窗,不再留恋海棠春色。
5
第二日,西院的客人启程告别。
一个富贵人家管家打扮的人,拿着一个盒子前来拜谢。
「我家公子病已痊愈,他说叨扰小姐多日,给你添了许多麻烦。」
「万望小姐收下这份微薄谢礼,以宽慰其心。」
我让雨玲收下,又让忠伯将他送了出去。
雨玲在我面前,打开了那个盒子,我见那画轴,隐隐觉得不对。
靠近一看,不觉眼下一热,头皮发紧。
莫说这是薄礼。
就是拿来做国礼都太过贵重。
「小姐,这是……洛神赋图。」
雨玲怔怔地叹道。
《洛神赋图》为东晋画家所绘,乃无价之宝。此画一直被宫内收藏,是官家的心头之好。我三番四次求皇后明颜姐姐好久,都未曾如愿看上一次。
能有幸观瞻,便此生足矣。
眼前这份礼物太过烫手,我必不能收下。
「雨玲,去请。」
半晌过后,一个身着白衣之人从院外走了进来,静立在海棠树下。
那人神容如玉,如亭亭松柏。
「姝妤见过十二王爷。」
我向他福礼。
他淡然一笑,眼底满是温柔神色。
「不必拘礼,我与你父亲原是旧时同僚。」
「宗老德才兼备,谦逊低调,是大梁不可多得的人才,我素敬之。」
父亲被罢官发配这些时日。
我看尽了人心不古,世态炎凉。
旁人都对父亲绝口不谈,从未想过,有人还念着他的好。
虽是只言片语,可切实带来了久违的暖意。
「姝妤替父亲谢过王爷。」
十二王爷顾兰舟原是官家一母同胞的弟弟,因姿容出众、天资聪颖曾被先帝议储。
他曾任开封府尹一年,短暂与我父亲在官场上有交集。
可他本人却唯爱老庄,闲云野鹤。
全无经世致用之心,一心只想当个闲散王爷。
母亲为我选婿时,也曾属意过他。
那时太后已故,他人品贵重,才貌双绝,又不涉党争,是最佳的贵婿。
只可惜三年前。
王爷向相府下聘礼时,官家已指给了他一位外邦公主为妃。
官家的意思是他若要娶我,可效仿娥皇女英,把外邦公主和相国千金一起娶了,平起平坐。
十二王爷断然拒绝了官家的提议,始终不肯娶外邦公主。
等他动容了官家时,已是一年以后。
我早已十里红妆,嫁入了晏府。
世间的阴差阳错,从未停歇。
「王爷,洛神赋图乃无价之宝。」
「姝妤只是暂借草屋茅舍供王爷小住,不敢收如此厚礼。」
王爷一顿,轻咳嗽了一声。
「雪庐在此地,如同沙漠之绿洲。若非你心善,小王还不知要缠绵病榻多久。」
「这稀世之宝若是无人欣赏,白放着也是空余寂寥。」
「宗小姐是收藏界行家中的行家。」
「洛神赋图能遇到你这般的主人,才是它最好的造化。」
雨玲脸上带着盈盈笑意,与其余几名小丫鬟一同捧着盒子,便不肯放下了。
「姝妤竟不知王爷如此好口才,是个天生的说客。」
王爷无奈地一笑。
「不知,今日是否有幸与你一同赏画?」
那道人影立于海棠树下。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翩翩君子,世无其右。
春光如许,何以相负?
「能与王爷一同赏画,是姝妤之幸。」
洛神赋图在我面前徐徐展开,我踱步看去,竟感受到了时光的交叠。
我全神贯注地赏画。
不知不觉竟有一朵海棠花落在我的乌发上。
待要拂去,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替我摘掉了那朵海棠。
我浅浅回眸。
竟是第一次知晓一眼万年的滋味。
6
那天,我还是坚持让王爷带走了《洛神赋图》。
毕竟,无功不受禄。
赏画之后,王爷也再未来过雪庐。
想必他已经心灰意冷,早早回京了。
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一浪高过一浪。
我托镇国公府的小公爷我表兄王佑安,揪出了晏相门生蔡淳、曾卞,借改革之名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证据。
官家大怒,一连撸掉了蔡淳、曾卞的参政之位。
与此同时,我兄长宗格非整顿京中军务有功,从京营节度使旋升九省都检点。
兄长给我传来密信,说是听官家的口风,父亲被召回京中有望。
兄长说原本以为十二王爷闲云野鹤,不问世事。
没想到他竟这样为父亲四处奔走,上下打点。
单读这几行字时,我已百感交集,心中涌起无限波澜。
管家来报,说是王爷登门拜访,已在雪庐外久候多时。
我让人把王爷请进来,他仍是一袭白衣,气度非凡,姿容胜雪。
「一月不见,王爷倒是清瘦不少。」
他无奈一笑。
「何止一月?是整整三十七日未见。」
我一怔,脸禁不住灼烧了起来。
「是啊,院子里的海棠都谢了。」
我抬头望着雪庐内的满眼绿意,似是嗟叹。
「在我心中,盛京的海棠从未曾凋谢。」
说罢,他便从怀中缓缓拿出了一支并蒂海棠步摇,那步摇上的海棠花瓣竟是粉色和白色的和田玉做的。栩栩如生,闪着细腻温润的光泽。
「胭脂为脸玉为肌,未趁春风二月期。」
「那年,我已错过了一次海棠盛放,悔恨不已。」
「余生,不想再错过第二次了。」
庭院内微风浮动,我静默良久。
只看到王爷眼中炽热的光亮,渐渐黯淡下去。
雨玲在一旁,无比替我着急。
「兰舟。」
「那我以后日日戴着这支步摇可好?」
王爷一怔:「只要你愿意,怎样都好。」
我粲然一笑,侧了侧发。
一只玉质修长的手,将那支海棠步摇稳稳簪入了我的发髻。
正在此时。
院落门口传来一声陌生又熟悉的声音。
「姝妤。」
我回眸一看。
海棠树下,竟站着一位故人。
若是从前,他下朝回了府。
雨玲一定第一时间给他递上洒了玫瑰露的热手帕擦脸,泡上七分热的小龙团。
我会笑着与他说,今日收到了哪些不易得的藏品,又碰上了哪些趣事。
只是,物是人非事事休。
我对他,早已了无牵挂。
「晏大人,不知今日到寒舍所为何事?」
7
晏挺之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的目光停留在我鬓边的海棠步摇上。
眼里是难以遮掩的妒意,却不得不向王爷行礼。
「王爷。」
王爷一脸玩味,却始终谦和。
「晏大人。」
我们三人坐在了雪庐的茶舍庭院里品茗,院子里安静如许。
晏挺之环顾四周,开口打破了这异常的静默。
「雪庐虽小,却与相府摆设全然一致。」
这「相府」二字倒是用得甚妙。
相府本是宗府,若是旁人乍听恐怕要误会为晏府,像我仍留恋他。
我看了眼王爷,只见他从容地握着青玉茶盏,抿唇笑了笑。
「晏大人眼下正有一桩喜事,我倒是要恭喜。」
「听闻太晟府大乐司之女临盆在即,恭喜晏大人喜得麟儿。」
尹清月的父亲因她未婚有孕,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
尹清月无家可归,晏母便偷偷将其接回了晏府待产。
这于晏家与尹家,都绝非光彩之事。
晏挺之险些洒了杯中的茶水,他深深叹了口气。
「王爷,我与姝妤之间误会颇深。」
「还请给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单独聊聊。」
王爷笑了笑。
「晏大人,姝妤才是雪庐的女主人。」
「你若有事与她商谈,也应提前找人通传一声,再登门拜访。」
「别忘了,她已与你和离。」
说罢,王爷将茶盏放下,离开了雪庐。
晏挺之红着眼睛看我,眼里满是不解。
「姝妤,短短三个月,你竟能忘却我们三年的时光与情爱吗?」
我轻笑。
「晏大人,男子立于世,向来是比女子多出许多自信的。」
「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拥有过的女子,这辈子都是忘不了自己的。」
「可我觉得,古往今来,女子都并非痴情。」
「只不过她们手中砝码与男子相较太少,太无路可选罢了。」
我放下了自己手中那杯茶。
「我若上嫁入宫,成为天子妃妾,那我也无路可选。」
「可我父母疼我护我,给了我下嫁之自由。」
「你与我成婚三年,你却始终未摸透我的脾性。」
「若男子不忠,哪怕他才高八斗,貌比潘安,我宗姝妤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更何况你?」
8
父亲的赦令是在九月下来的。
新政虽好,却敌不过各层官员为谋私利,层层盘剥,搅得百姓水深火热。
官家重任我父亲为宰相,晏父则被罢官,赋闲在家。
宗府门前又重现了花团锦簇、烈火油烹的日子。
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宗家挨过了怎样的无明暗夜。
一年一度宫廷芙蓉宴,京中八大公侯王府、高位品阶的官员及女眷都盛装出席。
尹清月挺着八个月的孕肚,正式在社交场上亮相,晏挺之陪在她身侧。
我刚看到他们,便听到了身后传来一阵爽朗笑声。
「姝妤姐姐!」
我回眸一看,一个穿着红色大氅的明媚女子绕过曲水澜庭,向我而来。
明眸皓齿,一抹朱唇。
可不正是护国将军府郑家二小姐郑如颜吗?
「妹妹!」
郑将军府与镇国公两家世代交好。
我与明颜、如颜是从小便在一处的闺中密友。
只是明颜姐姐四年前入宫为后,如颜随父亲去蜀中游历,我们已有一年多未见了。
她亲昵地握住了我的手,眉眼之间都是喜悦之情。
「姐姐,你让我想得好苦!」
我刮了刮如颜的鼻尖嗔她。
「过了年可都满十六了,怎还是这般小孩子心性?」
她也不在意,只盈盈一笑,腮边两只小梨涡尽显,娇憨明媚。
让人看了心底就明亮了起来。
「姝妤姐姐,你做得真好。」
她凑近了低声道。
「我姐姐说,天下女子除了你,再没人有这般的气魄!」
我抿了抿唇。
「我并不是个好榜样,天下女子可莫要学我。」
如颜目光灼灼。
「那是天下女子都没想过,女子还能这般活!」
如颜说罢便红了眼眶。
「我父亲兄长为顾氏一族打下江山又如何?」
「官家娶我姐姐做皇后,也与她缱绻多年,到最后不还是左一个贵妃,右一个昭仪的。」
「姐姐当了皇后又如何,还不是如履薄冰,整日在虎狼窝里斗!」
如颜的眼泪沾湿了衣襟,我便替她擦去眼泪,哄着她。
「我们姐妹好些时日不见,怎的一见面就哭得跟个小花猫似的?」
「我是替姐姐们委屈!」
我浅浅一笑。
「明颜姐姐是皇后,自有她的职责所在。至于我……我不委屈,不过妹妹既为我伤了心,我就勉为其难,为妹妹接些金豆吧。」
说罢,便将扑流萤的团扇,伸到她脸颊下给她接着泪珠。
如颜这才「扑哧」一声笑了。
「满盛京就数姐姐最坏,从小到大贯会笑我。」
见她脸上恢复了些神色,我心里才松乏些。
我们身旁不远处,晏挺之为尹清月题了一首小词,引来众人的羡慕称赞。
如颜面色讥诮。
「姐姐,我听闻宴挺之只给了尹清月媵妾的名分,她倒也肯。」
我微微勾唇。
「人贵自重,她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旁人也无可奈何。」
我看向树上挂着的纸笺,寻今日芙蓉宴的谜题——是曲牌名《九张机》。
9
尹清月走累了,晏挺之与晏母一同陪她在德风亭里纳凉。
这些时日,朝中势力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宗家东山再起,晏挺之在官场上处处掣肘,很不好过。
晏挺之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落在宗姝妤身上。
她依旧灼灼风华,灿若骄阳,所有人在她面前都会黯然失色。
「晏郎,你在看什么?」
晏挺之抿了口茶。
「没什么,一会儿我们要不要去看看芙蓉宴的谜题?」
「晏郎是堂堂进士,我只略识得几个字罢了,看账本倒还可以,吟诗弄赋,倒是勉强我了。」
晏挺之脸上未免有些失落之意,尹清月只得为他斟茶。
她轻颦浅笑,抬头一望,竟看到十二王爷向宗姝妤走去。
尹清月不由得皱起了眉。
这位十二王爷谁人不识?
俊逸出尘,闲云野鹤,不问朝政。
因是官家一母同胞的亲弟,倒被赐予了最尊贵的亲王爵位,在南临享有最丰饶的封地。
这些年,多少公孙王侯家的女子都思慕王爷,想和南临王府联姻,王爷都拒绝了。
难道……
不可能,她宗姝妤再高贵,也是和离之女,废弃之身!
她与挺之和离,这辈子就算是完了,难道还能去做王爷的侧妃?
真是痴心妄想!
在场的所有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王爷与宗姝妤身上。
连官家和皇后都忍不住向他们侧目,气氛已很不寻常。
晏母脸色阴沉地坐在德风亭里,怒目看向曾经的儿媳。
「不知羞耻!」
晏母不像宗家主母王氏,出身镇国公府,凭着一个好娘家,连状元郎出身的宰相竟就这一个妻子,从不纳妾。
晏父算得上不喜女色,可后院里也有两个姨娘,这些年让她受了不少气。
她更看不惯王氏的女儿嫁到晏府,那相府千金、金尊玉贵的做派。
让她全然立不起这婆母的款儿。
晏母原想趁儿媳三年未生育,宗府式微,给她个下马威。
没想到,这到手的金凤凰,竟这么飞了。
换了个小门小户家的女儿,尹清月一入府,晏父便丢了宰相之位,未免让人觉得晦气。
尹清月见晏母脸色不好,马上给她倒了杯茶。
「夫人,您别生气。」
「姐姐若是顾念宗府与晏府的脸面,断不会做出任何辱灭门风之事的。」
晏母扫了一眼尹清月,尹清月便不敢再说话。
另一侧,王爷的十三弟北靖王顾兰亭借了一步与他说话。
「皇兄,这宗家大小姐纵有千好万好,却是出了名的善妒!」
「她可是夫君纳个小妾,二话不说就要和离的主儿。」
「若天下女子个个都如她那般,我们男子还有安身立命之地吗?」
「皇兄,你可万万要想清楚了!不可错付深情!」
王爷忍俊不禁。
「兰亭,我若说,我最爱的就是她这副性子呢?」
顾兰亭怔了一怔,眼中满是不解。
「这世道原本就对女子不公。」
「男子不能明知自己在这世道之中占尽了便宜,还要让女子笑着承恩吧?」
「那天她浩浩荡荡离了晏家。」
「赌上自己全部身家性命,也要为天下女子辩一个理,争一口气的决绝,实在令我钦佩。」
王爷坦然地一笑。
「我亦是好赌之人,这一生,我陪她一起。」
10
芙蓉宴的人越来越多,我摘下了纸笺,提笔写下诗词。
「一张机。」
「朝起梳妆试春衣,雪庐萧瑟心绪凄。花如雨落,悠悠琴笛,不敢问归期。」
王爷不徐不疾地站在我身侧,执笔写下一句。
「二张机。」
「沧海桑田心如一,洛神女临洛水溪。观影自照,纷纷海棠,余韵胜往昔。」
此时此刻,官家与皇后也笑着凑到了我们写诗的地方。
我继续落笔。
「三张机。」
「娥皇女英未敢依。宋玉东墙未敢期。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谁人配白衣。」
王爷看向我的眼里尽是温柔。
「四张机。」
「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穷无极。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白首不相离。」
……
如颜站在晏挺之身侧,笑着问他:
「晏大人,你说王爷和姝妤姐姐是不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啊?」
晏挺之淡笑了声,低声道:
「王爷怕是痴心妄想,姝妤再怎么落魄,也断不会为人妾室!」
晏挺之暗暗握紧了自己在袖中的手。
他何尝不是在赌?
赌姝妤切切实实认清了现实,才会想起他的好。
她最后总会知道,做晏夫人于她,是最好的选择。
就在此时,王爷此时向官家皇后请旨。
「皇兄皇嫂,兰舟一生寄情山水,从无定性,如今别无所求,心中唯有一女子,视若珍宝……」
宗家与晏家、满盛京的公侯王孙、高门主母、千金小姐、无数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我与王爷。
「难道她宗姝妤要给王爷做侧妃?」
「侧妃已经不错了,养在闺阁中未出嫁的女子才如珠如宝,她是什么?」
「宗姝妤才貌双全又如何?和离再嫁,残破之身,难不成还想为人正室?」
「要是我啊,就出家当姑子去,又不是没了男子不能活,倒也不至于白白成了满盛京的笑话。」
我笑了笑,对周围一切声音都置若罔闻。
只听兰舟道:
「希望皇兄将宗宰相千金宗姝妤赐予我做——临南王妃。」
此言掷地有声。
芙蓉宴上,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晏挺之脸色苍白,恍然间像失了魂魄。
尹清月在他身旁已经站不住了,她紧紧地捂住了肚子,身体禁不住后仰。
晏母气愤地看向我与王爷,拂袖而去。
如颜妹妹眼中含泪,击节称赞。
官家笑了笑,看向皇后。
「皇后以为如何?」
「臣妾以为,王爷钟情姝妤妹妹多年,痴心不改,令人动容。」
「王爷与姝妤妹妹才学家世,性情容貌,无一不配,乃佳偶天成。」
「请官家成全这段金玉良缘。」
官家笑了笑。
「那朕就依皇后之言!下月初一,宗相嫁女,南临王娶亲,必要办得风风光光,朕与皇后定要和皇弟、弟妹讨一杯喜酒喝。」
我与兰舟向官家皇后谢恩。
天空中刚好有一对大雁成双飞过,夕阳像镀上了一层细碎的金箔,绚烂无比。
从今往后。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11
宗府海棠西院内厅,如颜,还有一众宗府小辈女眷们商量着新嫁衣的绣样。
忠伯从外院进来,在一旁揣着双手,一脸为难。
「什么事?」
「小姐,晏大人还是不肯走,外面下着那么大雨……」
如颜气得脸通红,她狠狠拍了下桌子。
「官家都给姐姐赐婚了,他怎么还有脸纠缠姐姐?忠伯,你告诉晏挺之,他要是再赖在宗府门前不走,我就让护国将军府的府兵打断他的腿!看他还敢不敢造次!」
忠伯忙摇着头:「哎哟,二小姐,这可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我看向雨玲:「给姐妹们拿些荔枝蜜,至于如颜嘛……」
我用扇子给她扇了扇风:「还是蜜瓜冰酪最得宜,能降一降火气。」
如颜这才回过味来,追着我。
「好啊,姐姐,我是替你说话,你竟这般笑话我!」
我笑得直不起身,不再躲她。
丫鬟们陆陆续续上了甜品冰点,我把女眷们都安顿好,看向忠伯。
「让他去西院茶室等我吧。」
我走过内廊,细听窗外雨声潺潺,空气里都是潮湿的气味。
再见到晏挺之时,不觉一惊,不过三五日的工夫,他消瘦了许多,人愈发清隽了。
遥想当初,我何尝不是被这副好皮囊迷了心?
他让小厮把我留在晏府的藏物,一件件拿了出来,竹简、甲骨、玉器……无一不承载着我们彼此的似水流年。
「你走时……只带走了自己来时的嫁妆,这些东西原本也有你的一半,你挑自己喜欢的,留下吧。」
「晏大人,你带来的所有东西,我一件都不会留。」
晏挺之眼底微微见红,他正襟危坐,似有千言万语,却都如鲠在喉。
「姝妤,你竟要绝情至此吗?就连一个念想……都不肯留?」
我平静地看向晏挺之。
「我若思慕一男子,便满心满眼都是他一人,心里再无其余缝隙留给他人。」
「如今我心中唯有兰舟一人……」
我双手扣上了面前精致的漆木盒子,推向晏挺之。
「断不会再留恋从前半分。」
说罢,我便起身。
一回眸便看见顾兰舟长身玉立站在茶室后面,眸光清幽,微微勾唇看向我。
我面上一热,剜了他一眼,又看向忠伯。
「怎的不知通传?」
忠伯被我噎住了:「小姐,是王爷说……」
「这宗府西院究竟是王爷做主,还是我做主?」
忠伯低头不再说话,我平了平心,提醒他:「好生送晏大人和王爷出府。」
说罢便留给他们一个背影。
王爷往前追了两步,又回头看向忠伯殷勤嘱咐道:
「好生送晏大人出府。」
12
十月初一,我从相府出嫁,长宁街上绵延十里红妆,万人空巷。
人人都说宗家大小姐命格极好,是天生的王妃命。
我却更担心,我那数十箱的甲骨、青铜器、竹简经不经得起这三番四次的折腾。
我大婚当日,尹清月生了个儿子,求仁得仁,如愿被抬为了平妻。
只是晏挺之早已回到洛阳,没有陪在她身边。
晏挺之在洛阳又找了个秀才的女儿,听说文墨皆通,长得与我有几分神似。
尹清月未出月子,便听说了那女子怀孕的消息。
说是别无所求,只求腹中晏家血脉能入族谱。
尹清月自那之后,容颜憔悴得十分厉害。
这晏家主母之位,也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好做。
母亲把忠伯给了我,入王府一并帮我打理府中事。
得益于忠伯事必躬亲,让我有了大把的时间作词,收录、记载我手中的珍贵藏品。
三年之中,我出了《咏棠词》《玉漱词》《宁安词》三册词集。
宗姝妤的名字,亦赫赫立在大梁群星闪耀的词人之中。
兰舟亲手为我在王府里种下了数百棵海棠,说希望我心中的诗情永不褪色。
二十二岁那年,我生下了我们唯一的女儿昭华。
昭华满月宴时,官家封她为永嘉郡主。
兰舟亲自教女儿读书认字,倒是让我有空闲躲懒,时常与姐妹们相聚。
昭华七岁时,兰舟送给了女儿一匹神气活现的小马驹,亲手为她做了一张弓,教她骑马射箭。
我则把自己收藏的文物都做成教材,教她认甲骨、识青铜、辨竹简。
《女训》《女诫》这样的书籍、兰舟视之为洪水猛兽,一概不让女儿碰。
夏日凉夜,我与兰舟一同在院子里消暑,片片海棠飞落在我们身上。
我们眼前摆着诸多史记经典、文学著作,我与他已赌了十题,胜负平分秋色。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
「庄子,逍遥游,第十七页,第三行。」
未等他翻书检验,我便自顾自拿起了茶盏喝了口煎茶,满口茶香。
兰舟笑着将我揽入怀中。
「姝妤,终究是你赢了。」
我笑了笑。
「余生与卿一起,输赢已不再重要。」
完